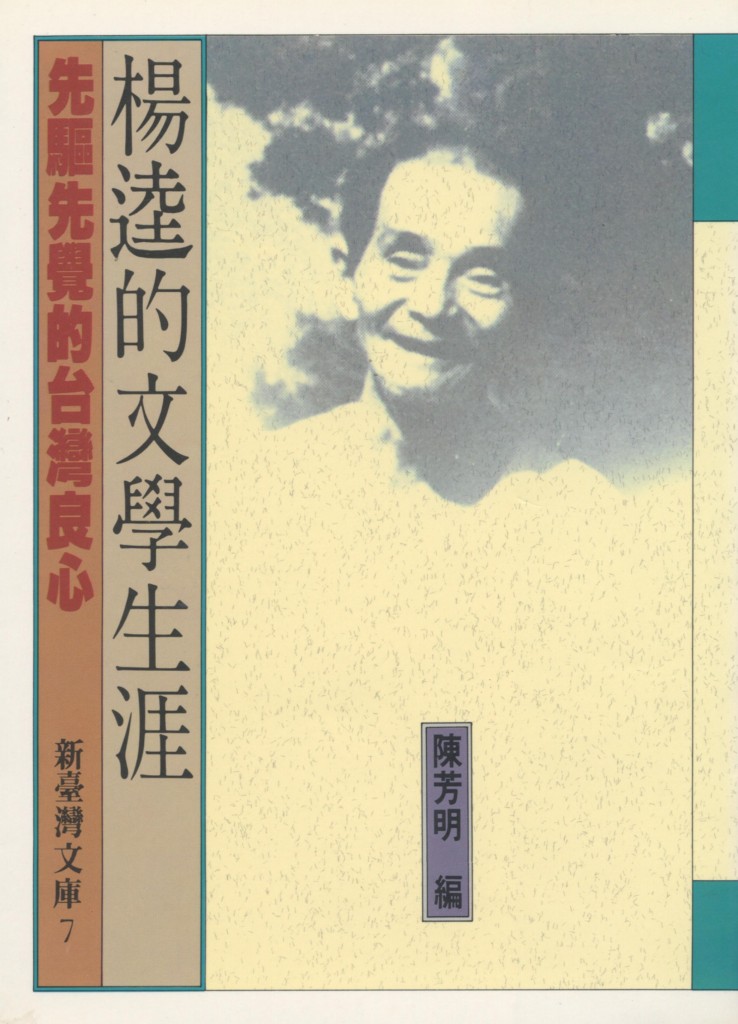楊逵的文學生涯
編者 陳芳明
序
楊逵,是台灣的良心。在政治運動中,他是一位先驅者 ; 在文學運動中,他是一位先覺者。他的行動與文字,深刻 表現了台灣人的反抗精神與性格,而且也為台灣人塑造了勇毅不屈的形象。他八十年的生命,芷好横跨了兩個等長的時代。他在戰前戰後的奮鬥,恰當地反映了台灣人追求光明前途的意志。本書共分兩部份..第一部收集他的文學品,包括他的小説「送報伕」、「鹅媽媽出嫁」、「模範村」等; 第二部份收入他的傳記自述以及各方的評價等重要篇章。這不是蓋棺論楊逵的書,而是一本瞭解楊逵文學生涯的重要選集。他的思想精萃盡在於斯。
他的一生有過幾次遠行。只有這一次,他走了,不再回來。也只有這一次遠行之後,他不再離開我們。他的精神,他的文學,完整且永遠留在我們身邊。
他並非沒有被遺忘過,曾經有過數十年,他與世界隔絕了。那正是他生命中最美好最成熟的階段,但那也是他最困頓最孤寂的時光。當我們記起他時,他已然接近晚年。生活了將近八十年的他,正好跨越了兩個等長的艱苦的時代。然而,眞正屬於他的時代卻從未到來。
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年,最後一季,最後一天,他仍然在期望那樣的日子。他的期望,不是坐待,而是追求。他的追求,終其一生。
自從第一次遠行之後,再也沒有人看見他退卻過,那年他二十歲,果敢並充滿野心,從殖民地台灣到達日本時,他就已經知道要選擇怎樣的道路。那並不是一次枉費的遠行。在那裏,有了一次刻骨銘心的體驗,他見證了殖民地母國的資本家是如何欺侮社會的弱小者,也目睹了弱小者是如何結合起來反抗不公不義。同樣在這一次遠行時,他初次接觸了社會主義, 這使他成爲日後台灣左翼政治運動的先驅者之一。他在理論中汲取了養分,而在行動中開花結果。回到台灣時,他二十二歲,時正一九一 一七年,台灣抗日運動發展到一個分合的路口。 他並沒有去尋找一份安身的職業; 相反的,他解下了知識份子的書巾,毅然投入波瀾壯濶的農民運動的行列。
他的性格帶著一種驕傲,這使得當年凌辱他的人,到後來都要感到自慚形穢。他的驕傲,並不是要豢養個人的尊嚴 ; 他總是忘記自己,而讓驕傲的性格化爲政治運動的一部份。唯其維持這種高貴的氣質,所以在他多次進出日本人的牢獄之後,仍然鬥志昂揚,毫不灰心。在 一九二〇年代的歷史圓柱上,他爲我們留下最好的台灣人形象的浮雕。
敏銳的思考,淸晰的觀察,是他的特徵。當他和他的同志捲起風暴時,他反而是冷靜的。 保持冷靜,是他再出發的動力。他也與他的同志決裂過,但是他的決裂並不澆熄希望,而是爲了點燃更多的火花。在風聲鶴唳的時代裏,當政治運動變得零落不堪時,他選擇了無聲的文學道路。他在晚年時曾經如此回憶:「我決心走上文學道路,就是想以小說的形式來糾正被編造的歷史。歷年的抗日事件,自然對我的文學發生很大的影響。」
他並不是第一個以文學形式來表達政治信仰的人;在這塊土地上,他卻是唯一把文學運動和政治運動做最完美結合的作家。他的作品,不是靜態的。他身處那個時代所感受的社會活力,都飽滿而充分凝聚在他的字裏行間。因此,從發表第一篇小說開始,他的文學就不僅僅是個人的,而是屬於整個台灣。
我們難以發現他細緻纖弱的感情。他呈獻給我們島嶼的作品,母寧是粗糙的、雄美的。 他靈敏的耳朶,總是聽見黑暗角落發出疾苦的聲音。他不必使用想像 ; 如果在他創作生涯中有所謂靈感的話,那絕對是來自他的經驗。他更不必使用裝飾的語言,他的語言其實是民間的、羣衆的。他篤信文學應該是根植於人民和土地,這說明了爲什麼每當他的作品問世時, 便很迅速發生廣泛的說服力。他從來也不必使用欺罔和誑騙的技巧,他一落筆,便是樸素和 誠實。在半世紀以後的今天,我們捧讀他的小說時,仍能準確感受他那時代的艱難與黯淡。
他沒有表現細緻的情,並不就等於他不瞭解愛。當他携著他的新娘去坐日本人的監牢時, 就足夠吿訴我們那是一個如何悲壯的戀愛故事了。他的小說沒有私情,有的只是擁抱台灣的 高尙情操。但是,在現實的生活中,他緊緊守著與他一起患難的妻子– 一位背叛纏足的、 肩負鋤頭的、沾滿泥土的女性。他們可能並不熟悉海誓山盟的私語:他們的愛的語言,表現 在受難時仰望鐵窗的每一刻盼望,表現在勞動時淌在田野的’每一滴汗水,表境在奔波時共同 迎接的每一粒星光。他們的愛,沉默不語.,像兩株佇立的玫瑰,彷彿各自迎風綻放,而他們的根鬚卻在土壤底下盤錯糾結在一起。
然而,歷史並沒有給他合理的回答。
在兩個時代交錯的叉路上,他對土地的愛又變成了新的罪。這一次,他開始了生命中最長久的遠行。那時他正跨入盛年,但是展開他面前的道路,竟是陰霾而曲折。在漫長的被遺忘的十二年中,他一無所獲;唯一的收穫,便是鍛鍊了更堅強的意志。他已經預見,他後生面臨的將是一個毫無許諾的時代。他也知道,沒有人能夠拯救他的土地,只有他和他的人民才是可以信賴的。他不知道什麼是嘆息,更不知道什麼叫做畏懼。在新時代的舊監牢裏,
他仍然堅持文學的勞作。他以兩倍心力寫出了陌生的漢文,只爲證明他對文學的力量仍具信心。在那些誠摯拙撲的文字中,他對酷嗜權力的腐朽人物,依舊保持嘲諷輕蔑的態度。他的體格瘦小,卻有著巨人般的人格。所有的壓迫者站到他面前,都一律變成侏儒。
他重見天日時,已近六十歲。結束這次遠行,他更必須挺著腰桿走出高牆,因爲在牢獄歲月中,他已知道島嶼變得更加傾斜,而歷史也顯得特別扭曲了。身爲一個受害者,他把憐憫和傷感全然擲棄在陰濕的牢房裏。他這樣說過:「憐憫和傷感是膚淺的,不能把讀者的感情變化爲意志和行動。」說這話時,他已坐過了十三次牢,而這正是他所遵奉的文學信念,也是他的政治信念。很少有壓迫者遇到像他這樣傲慢的思想犯吧。在經過長達十餘年的思想改造之後,他仍然坦白向世界宣佈自己是「人道的社會主義者」。他的宣稱,豈非是對一切加諸於他身上的汚辱做了有力的反擊?他不懈地堅持自己所信仰的思想,就足夠證明他和他的土地是牢牢站在一起的。
他深知,公平和正義還未降臨到他纏綿苦戀的島嶼。所以,他決定荷鋤上山,把最大的輕蔑留給他背後的權力者。他爲自己的農場取名「首陽」,稍有一些歷史常識的權慾人物,看到這樣的命名都應該覺得羞慚的吧。倘然他們站在首陽農場之前而不感到臉紅,那如果不是無恥,便是無知。縱然他後來又爲花園重新命名,但是他的首陽精神,已成了他生命的支柱。
這樣一位驕傲的人格者,也有謙遜渺小的時候。從一朶茁壯的玫瑰,他虛心學習了堅忍 不屈的精神。沒有什麼可以擊敗他,艱苦折磨的經驗,使他在任何環境都能萌芽、生長、開花、結實。也沒有什麼可以誘惑他.,在他看來,栽培一株花苗遠比追求名利重要得多。對於佔據要津的政客,他可能德到陌生;但是要他細數花園中所有的植物,他絕對能夠叫出每一朶花每一株草的名字。他把腐朽與芬芳區別得淸淸楚楚,一點也不通融。如果有人偶然看見他低頭,那不是屈服,他其實是正在埋首爲他的花園施肥。他用經營一篇文學作品的心情,去扶植一株玫瑰。但是,他揮汗翻土,辛勤澆水,並不是要去感動每一朶花,他只不過是爲 了使自己的背脊挺得更直。他要讓他的土地知道,一顆社會良心依舊充滿了活力。
他身在山上,心存人間。在晨霧中,在暮靄裏,都可看到他工作的身影。勞動,不停的勞動,成爲他生命的最後的據點。可是,他的眼睛始終注視世事的一切變化。他以一朶壓不扁的玫瑰自喩,而且也終於成爲年輕知識份子的普遍認同。他支持每一位追求公義的人,但他不以指導者自居,他參加他們。他跨過七十歲時,還蘊藏著少年時期的奮鬥與憤怒。反抗的意志使他昇華爲這個時代的象徵–一朶玫瑰,成了他的名字的隱喩。
然而,歷史還是沒有還他一個公道。直到不吿而別的那天,他苦戀的島嶼仍然還是傾斜著,他沒有看到它被扶正過來。他可能覺得遺憾,但不必感到抱歉。這樣龐大的工作,顯然 不是他一個人所能完成的,而且也不只是他一個人的責任。對於這個人間,他完全沒有一點虧欠。可是,這不能說已經銀貨兩訖。他付出本分,還透支了精力,我們虧欠他太多了。他曾經被奪走的光陰,更不是我們能夠補償的。我們悲傷,因爲他的離去將使塊這土地寂寞了些。但我們也應感到僥倖,因為他留下來的工作,恰好是我們能夠繼續完成的。倘然有人退縮卸責,宣稱難以繼承這樣的工作,那就不只是羞愧而已,簡直是一種罪惡。
這一朶玫瑰,以盛放的姿態離去。那天他要遠行,再次顯露他豪放的性格,在淸晨霧氣 中說走就走,絲毫不拖泥帶水。他已習慣那混沌的霧,正如他熟悉那兩個顚倒錯亂的時代。 他的去和來,將成爲這塊土地永遠的傳說。假設若有人問起這朶花的來歷,我們都知道他屬於常綠灌木,學名叫楊逵。他選擇出發的那天,是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
編者 陳芳明簡歷
台灣左營人,1947年生。1969年輔仁大學歷史系畢業,1973年獲 台大史學碩士,1974年赴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深造。除本行的史學硏究之外,他以「陳嘉農」筆名寫詩和散文,以「宋冬陽」寫文學評論, 以「施敏輝」寫政論,並歷任海外〈美麗島週報〉編輯,<台灣文化>總編輯,「台湾文庫」執行主編,是海外反對運動一支健筆,因此長列「返台黑名單」達15年之久。
著有《鏡子與影子》《詩和現實》《受傷的蘆葦》《放膽文章拚命酒》
《台灣人的歷史與意識》《在美麗岛的旗幟下》《在時代分合的路口》《鞭傷之島》《台濟內部民主的窺探》《台灣對外關係的窺探》《謝雪紅評傅》。
編有《台灣意識論戰選集》《楊逵的文學生涯》《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台灣戰後史資料選–二二八專輯》。
Posted in 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