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傷的蘆葦
作者:陳嘉農
因爲這是一份白皮書,我不能不藉這册散文集來宣吿對舊日的遺棄,並且也嚴重警吿自己日後應更無情鞭笞自己。對文學生涯的追求,始於我二十歲那年。今年,時間已逼我跨越生命中的四十歲。我在文學創作上的努力,僅收穫了這一册散文集。這種疏懶,這種怠惰,已違背當初出發時的誓願。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爲這樣的爽約辯護,也沒有任何藉口可以爲這樣的負信開釋。如果能夠解釋爲何我的產量如此稀少,那應該歸咎於我對文字掌握的能力過於欠缺,以及我思想的成長過於遲緩吧。跨過中年的分水嶺,對自己提出了白皮書,自然不能掩飾長年以來的過失。不過,也正由於有前半生的懈怠,我才能夠以更警醒的心情經營我的後半生吧。
因爲這是一份精神地圖,在散文裏有我走過的道路與選擇的方向。這十年中,我的思考有過幾度轉變。如果那轉變是可喜的,那是因爲我找到了島嶼的方向。一九七四年離開臺灣時,我的行囊裏裝滿了一顆雄心。那時,我決心要爲臺灣描繪一幅遠景,也要爲島嶼尋找歷史的答案。十年之後,一顆心仍如焦渴的炭火持續燃僥,只是那份心情比較趨於落實,伹有時又覺得落單。對自己歷史的無知,曾經使我懷抱過一個碩大無朋的巨夢。現在回首看來,無論那夢是如何虛幻,終究是每一位臺灣子弟無可避免要經過的階段。唯一不同的是,有人把這個階段拉長,有人則將其縮短。我之所以感到落實,是因爲我超越了這個階段,從此不再迷惑於盛唐或江南的華麗假象。我之所以感到落單,則是因爲我同輩的一些朋友,仍然滿足於一顆過度膨脹的心。往往是這樣的一顆心,使他們與島嶼的命運脫節。而這些朋友卻反而回過頭來,視我爲分歧份子。倘然我是一位異議者,那是因爲我認同臺灣之後的一個必然結果。爲此,我了無遺憾。
如果給我機會重新出發,我還是會選擇敎育體制外面的這條歧路,一條充滿崎嶇卻有着出口的歧路。我曾經是島上敎育體制的受害者,我的年少歲月都虛擲在知識追求的迷陣中。這份精神地圖,便是在摸索與試誤的過程中拼寫出來的。我要讓我的朋友看到地圖上的陷阱與死巷,也要讓後來者看到地圖上的錯誤與虛構。設若他們能夠按圖索驥,少走枉費的道路,那麼我的受害,就是我的受惠了。
選擇散文的形式來表達這幾年的思考,只是我嘗試各種文體撰寫中的一種。自一九八〇年以後,我使用了至少十個以上的筆名。埋名隱姓,是這個時代的苦悶象徵。只要對我的島嶼有所幫助,則具名或者是佚名,已屬次要的事。不過,這兩年來,我比較固定於三個筆名,亦卽寫政論的施敏輝,寫文評的宋冬陽,寫詩與散文的陳嘉農。這已是公開的秘密,我無需「護短」。至於秘密的部份,則任其隱沒下去。當初爲什麼要使用這麼多筆名?我相信,只有這樣畸形的時代才能解釋了。
對於散文的分類,我粗略劃爲兩種,一是周作人式的,一是魯迅式的。前者言志,後者載道。周作人的文章,充滿書巾氣。傳統士紳的閒情,都可在周作人的散文中找到影子。甚至,閒得有些腐朽。魯迅則不然,他的文風屬於草莽性格,彷彿是江湖浪子,不向任何權力低頭。周氏兄弟,領導三十年代中國文壇,儼然成爲兩個集團。値得注意的是,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們的重要弟子選擇了兩個極爲相反的道路。走周作人路線的文人,如果不是隱居,便是投靠日本人。追隨魯迅的作家,則參加延安的左翼革命運動,或抗戰游擊去了。文格與人格的關係,似乎可以在周氏兄弟的身上得到印證。
我自然是偏愛魯迅的。他的文字,剛強裏帶一份柔情,哀傷中夾一份悲憤。行文過處,都是力量。我必須承認,讀過魯迅之後,使我擺脫臺灣敎育體制釀造出來的酸腐之氣。而更重要的,魯迅使我正式確認自己是臺灣人。因爲,帶給他一生坎坷命運的統治者及其體制,對他的土地而言,畢竟是過去了。然而,同樣的體制,於我的土地卻還是方興未艾。魯迅如果也是臺灣人,他當能體會我與我這一代的心情。
載道的散文,在臺灣尙未建立起傳統。戰後臺灣散文的主調,仍是沿着抒情的路線發展。在抒情散文中,有相當多的創作者,有意爲旣有的體制護衞。據說他們與政治是絕緣的;但是,權力者頒賜給他們的價値觀念,卻又照單全收。他們的散文遠離社會,因爲他們對不公不義視而不見,他們也宣稱不談政治。如果他們稍有激烈的言詞,也往往只是反貪官,不反皇帝,最後又接受招安去了。載道的散文在臺灣難以立足,並不能說權力者過於成硬,而是創作者過於軟骨。向權力者低頭的結果,使他們寫出的感情也是帶有體制性格的。他們珍惜自己飽滿的情感,懼於探險,畏於挑戰。如果他們的創作具備抵抗精神的話,那麼他們抵抗的是社會上的抗議聲音。
臺灣,曾經是無聲的。到了七〇年代以後,才漸漸出現了吶喊。臺灣的文學工作者,卻總是落在社會的後面。當街頭上的運動澎湃洶湧時,他們卻以文字引導年輕人遠離土地與人民。有墮落的文人,才有墮落的文化。無聲的臺_,是這樣創造出來的。我曾經也參加沈默的行列,躱在知識的硬殼裏,龜龜瑣瑣表達一些空泛的觀念,零零星星吐露一些泡沫的情感。我的土地長期受到重創,我其實也是幫兇之一。
疏離自己感性的一面,過濾過剩的自我情緖,是我八〇年代以後嘗試去做的工作。我並不認爲,散文創作必須要有一定的格式與方法。我也不認爲,華美的文字,洗練的技巧,就能構成完美的散文。以社會現實來檢驗散文中的思想,應該是較爲迫切的事吧。這樣說,我並不主張所有的創作都必須穿制服,都必須步伐一致。我的意思是,一位作家在不公不義之前,如果一語不發,或甚至去歌頌權力者,那麼他沒有理由不受到譴責。現階段的臺灣,絕對不是一個常態的社會。如果有作家敢於宣稱他不了解這個社會的動亂,我只有加倍佩服他的鎭靜與自私。
爲了我這幾年來寫出臺灣社會的鎭壓與抗議,權力者竟然使我失去了國籍。他們以爲,切斷我返鄕的道路,便可以切斷我的咽喉。他們以爲,割裂我的親情,便可以割裂我的人格。對於十餘年來所寫下來的每一字每一句,我都可以負起全責。當他們拒絕續簽我的護照時,竟然懼於說出拒絕的理由。那位有着發亮前額的據說是外交官的辦事員,以着頗有尊養的語氣拒絕爲我的護照延期時,面容仍然帶着微笑。對他來說,把臺灣子弟關在島嶼土地之外,彷彿是一件溫文有禮的事。這次不快的經驗,使我第一次體會到他們如此酷嗜權力的原因。不過,這位西裝革履的辦事員,終於凝住了微笑。原因很簡單,我拒絕鞠躬作揖。低頭,是他應該做的,絕對輪不到我。
我依據我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寫下我的見證。我表達我的憤懣,這是做爲島嶼子民不可剝奪的權利。我熱愛我的土地,這也是臺灣子弟不可分割的情感。國籍是他們的,土地是我的。經過漫漫十年的光陰,我終於找到自己的土地,卻又失去了國籍。這當然是無可奈何而又諷刺的事。只是,我相信,一位回航的浪子,終有受到接納的一天。今天,我向島嶼呈獻這一册散文集,不僅是要結束我沈淪的舊日,而且也要宣佈,終有一天我要爲我的精神地圖重新命名。這個名字,必然是全體臺灣人共同創造的。我堅信,這個日子就要到來。我的堅信,來自我長期不毁的意志,從揚眉的少年到橫眉的中年。
一九八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聖荷西
作者:陳嘉農
 陳嘉農,本名陳芳明,高雄左營人,一九四七年生。現為美國「台灣文化」總編輯,華盛頓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他另以筆名宋冬陽,撰寫文學評論與歷史傳記;也以筆名施敏輝,撰寫政治評論。他的散文,對我們的島鄉充滿感激之情,允為這個放逐時代之放逐文學的代表作。這本書,是他浪跡海外十餘年的備忘錄,是他做為自我警惕的白皮書,也是他生命重整改造的一份精神地圖。
陳嘉農,本名陳芳明,高雄左營人,一九四七年生。現為美國「台灣文化」總編輯,華盛頓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他另以筆名宋冬陽,撰寫文學評論與歷史傳記;也以筆名施敏輝,撰寫政治評論。他的散文,對我們的島鄉充滿感激之情,允為這個放逐時代之放逐文學的代表作。這本書,是他浪跡海外十餘年的備忘錄,是他做為自我警惕的白皮書,也是他生命重整改造的一份精神地圖。
Posted in 2014/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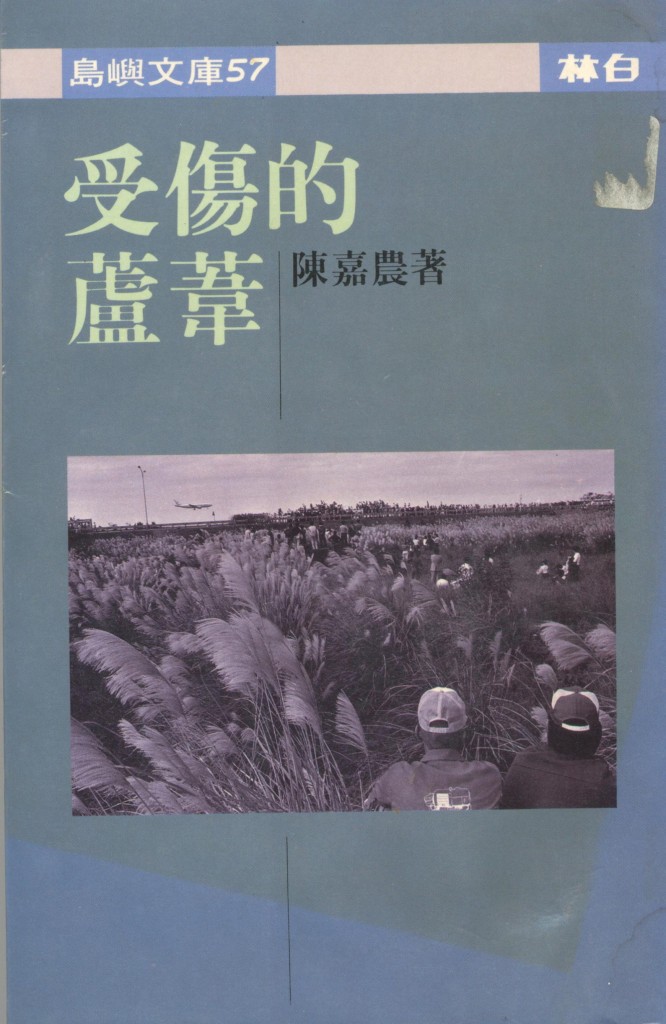 這册散文集,是我浪跡海外十餘年的一份備忘錄,是我對自己往後生命警惕的一份白皮書,也是我思想轉折過程中繪製的一份精神地圖。因爲這是一份備忘錄,所以書中所收的文字,紀錄了我過去十年中情感與理智的交錯起伏。當一個人被置放於地球的偏遠角落時,許多情緖上的困頓與傷口,都必須依賴自己的心志去克服、去撫平。如果是在島上,我可以攜帶一顆受傷的心,到朋友的聚落處去取暖包紮。然而,在這荒涼的異域,面對的只是孤寂的時光。曾經有過一段日子,寧靜的湖畔、港夜的燈光、山谷的星火,或街角咖啡室的音樂,往往是我心靈曠野的低語者。離開家鄕以後,我便是這樣活下來的。然而,我掙脫了感傷的牢籠。在心路歷程的跋涉過程中,所有的挫折,所有的流言,最後都讓我當做磬石一般叠高起來,砌成一顆不碎不滅的信心。於今,翻閱這份備忘錄,昔日誤以爲是痛楚的打擊,看來已是多麼微不足道。牢記那些稚嫩的歲月,爲的是要走更爲艱難的道路。
這册散文集,是我浪跡海外十餘年的一份備忘錄,是我對自己往後生命警惕的一份白皮書,也是我思想轉折過程中繪製的一份精神地圖。因爲這是一份備忘錄,所以書中所收的文字,紀錄了我過去十年中情感與理智的交錯起伏。當一個人被置放於地球的偏遠角落時,許多情緖上的困頓與傷口,都必須依賴自己的心志去克服、去撫平。如果是在島上,我可以攜帶一顆受傷的心,到朋友的聚落處去取暖包紮。然而,在這荒涼的異域,面對的只是孤寂的時光。曾經有過一段日子,寧靜的湖畔、港夜的燈光、山谷的星火,或街角咖啡室的音樂,往往是我心靈曠野的低語者。離開家鄕以後,我便是這樣活下來的。然而,我掙脫了感傷的牢籠。在心路歷程的跋涉過程中,所有的挫折,所有的流言,最後都讓我當做磬石一般叠高起來,砌成一顆不碎不滅的信心。於今,翻閱這份備忘錄,昔日誤以爲是痛楚的打擊,看來已是多麼微不足道。牢記那些稚嫩的歲月,爲的是要走更爲艱難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