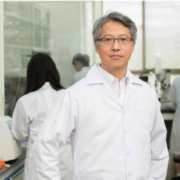憶名任
作者 林壽英
2007 年的七月初接到一通久未聯絡的屏東女中校友從洛杉磯打來的電話,告訴我當年七月十四日在南加州要舉行第九屆北美州屏東女中校友會,希望我能去參加跟校友們見見面。我們聊了一會兒,她突然問我說“妳知道吳名任在2005年過世的消息嗎?”聽到名任離世的惡耗,雖然不是完全意外,但不免十分震驚與難過,不勝唏噓。放下電話,我默然徘徊於家中的客廳與書房間,步伐一步緩慢一步,對名任的回憶層層交疊,幌如一場幻夢醒不過來。
一九五八年我在屏東女中上高中一年級時,高我們一屆有一個非常出風頭的學生,她不但人長得甜美漂亮,功課也異常出色,口才、人緣又好。我們這些學妹們都知道她叫吳名任,我對她羨慕得很,但並不真正認識她,在屏東女中時我也沒跟她交談過。但天地如此之大,人的世界卻是如此之小,沒想到二十幾年後,名任與我竟然在美國相遇。記得名任和我第一次相遇而開始真正認識是在一九八二年於紐奧良 (New Olean) 舉行的毒理學(Toxicology)學會的年會上。原來名任從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畢業來美國留學,與我來美國留學以後所學相似,職業方面所做也類似,當時名任在中西部 Ohio州一家很大的毒理學試驗公司 (Battele Laboratory) 就業,而我則在Illinois 州支加哥北郊的藥廠 (Abbott Laboratory) 做事。我在年會上一見到她就認得她就是那位鼎鼎有名的屏東女中校友吳名任,交談之下,才知道我們不但是屏女校友而且還有點遠遠的姻親關係,原來名任的夫婿(張逸勢先生)竟是外子的遠親及屏東、南州的同鄉。在屏東女中時,我知道名任是中國淪陷給共產党後才從中國來臺灣的 “外省人”,二十幾年後,她在美國第一次跟我交談時用的卻是非常輪轉的河洛話,使我吃驚萬分。她的河洛話講得非常到地,讓我這個來美國以後才開始學講河洛話的客家人自嘆不如。我問她怎麼她的河洛話講得這麼流利又富有“下港腔”,她笑著說她從小住在屏東鄉下,左鄰右舍都是講河洛話的台灣人,她從小就學了一口輪轉的河洛話。尤其她跟張先生結婚後,她的公公、婆婆只會講河洛話,她在家跟夫婿及家人也都講河洛話。我們一見如故,很快就成了好朋友,除了每年的學術年會時見面外,偶而也通通電話。
名任很開朗與我無所不談,從她的談話中知悉她在台灣沒有親生的父母親,她小時是跟從她的叔父母從中國撤退來台灣,她的叔父任職於屏東南州的糖廠,她由叔父母養育長大。當她跟她鄰近的一個台灣人的青年(張先生) 戀愛時,張先生的父母親及家人都非常憐惜疼愛她,她師範大學一畢業就跟張先生結婚。婚後幾年間,她生了一女一男,然後她決定出國來美深造,便把幼小的兒女托給夫婿及公公、婆婆照顧扶養。來美國兩年後,名任拿到碩士學位又在中西部找到一份工作時便把她的夫婿及兩個兒女接來美國團聚。後來名任的夫婿在中西部的Columbus, Ohio開了一家餐館,便把他的母親(名任的婆婆)接來幫忙。一向求學心重,努力上進的名任,這時就決定暫時離家到 Arkansas 州立大學 幾年求學攻讀博士學位。名任在拿了博士學位後,因一時在中西部找不到適當的工作,只得又繼續離家在 Arkansas州就業了幾年。等到她在回到中西部的Battele Laboretory就業,回家與孩子、家人相聚時,兒女已到了上初、高中的年齡。懂事的大女兒很能體諒母親長期離家的苦心,但小兒子對母親卻非常不諒解,認為他小時需要母親時,母親都不在身邊。名任為此感到無比的愧疚,對她兒子有一種無法彌補的自責。她常對我說若能從頭再來,她會花更多的時間來陪伴孩子,尤其當孩子小時、需要母親関愛的時候。
1990年初,台灣黨外活動發展蓬勃,與名任的夫婿張先生是大學校友兼朋友的黨外風頭人物康寧祥先生打算在台北辦黨外的報紙 — 首都早報,邀請名任的夫婿回台灣幫忙。那時名任的兩個兒女都已成年自立,名任便毅然辭去她在 Battele Laboratory的職務,跟夫婿回台灣為故鄉服務,她任教職及研究工作於桃園的長庚醫學院。名任每年都回美國看兒女及孫子們,並參加毒理學會的年會,名任和我也每年在年會時相聚見面。
2000年底,名任從臺灣寄來給我的聖誕卡上寫道她得了乳癌,正在化療中,身體許可的話她仍打算次年的三月底來美國參加毒理學會的年會。次年 (2001年)在年會中見到她時,名任看起來有點消瘦、蒼白,但精神很好,她笑著用河洛話對我說她現在是在“吊車尾”(人生列車的車尾),那是我最後一次跟名任相聚見面。我2002年從 Abbott 藥廠退休後,就沒再参加毒理學會的年會。此後名任與我偶而通電話或電郵,每次問她健康的情況,她總是以“吊車尾”來形容,我一直認為她是在 Re-mission中,祈求上天賜她健康。深為遺憾及內疚的是 2004到 2007年間, 我疏於跟名任聯絡,沒想到名任竟走得這麼快,連一聲道別都沒有,唯一感到稍微安慰是她安息在她心愛的故鄉台灣。淡去的暮彩映照,依然沒有告別,不知夢的盡頭,是不是清晨?我想,我們之間的友誼會因我對她的思念,永恆不息。
源自 林壽英 寫於Libertyville, Il,2007年 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