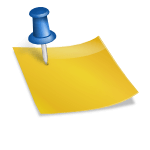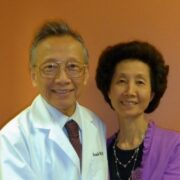他鄉已然成故鄉
作者 李建漢
前言:
歲月如梭,移民來美已逾36載,在這異鄉度過了幾近半生。近年屢次「返鄉」探望親友,卻越來越覺得像是去作客,不僅生活步調與人不同,許多話題也不太對味了。旅程結束,我們終究還是要「回去」在美國的家。這個他鄉已經成了我的故鄉。
回首走過的這條移民路,雖然辛酸苦辣備嚐,但也未嘗沒有歡欣喜樂。偶於夜半夢迴思及過往,會不禁感嘆自問為何當初腦筋突然「鏽多」註1,竟然放棄在故鄉台灣如日中天的事業,遠離親朋和好友,攜家帶眷冒然踏上前程茫茫的移民不歸路,押上人生最大的一注豪賭,到底所為何來?
如今年逾古稀,子女各自學業與事業有成,生活也美滿幸福,兒孫承歡膝下,樂享天倫之際,才頓悟眼前豈非輸贏已經分明?對於昔日的選擇非但無怨無悔,若要我重新再做一擇仍,押上一次抉擇,我仍然還是會投下同樣的賭注。
我没有顯赫的家世,更無傲人的學經歷,僅衹是一名出身艋舺的艱苦囝仔。雖然自忖才疏學淺寫不出感人的移民故事,但是仍願響應參與芝城台美人以集體寫回憶錄的方式,將自己在故鄉和異鄉的陳年舊憶及移民的心路歷程,以拙筆平實地回顧個人這段大遷徙的歷史。(註1:短路,short circuit)
身世與生平
〈恐怖的孩提時代〉
1940年我出生在日治時期的台北艋舺、新起町三丁目(今之長沙街的康定路與昆明街之間)鄰近清水祖師廟的新起公會隔壁。
我的孩提時代正值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事最劇烈的時候,從有記憶開始,就是跟著家人不分晝夜在躲避美軍的猛烈空襲,隨時都處於恐懼和掙扎求存的境況。我們不僅白天疲於奔命,我連三更半夜也常從睡夢中被拉起來逃命。記得有一天黒夜裡被叫醒來,衹見滿天烽火(當晚新生報社被炸,燃燒的紙張飛滿天際),當時以為我已經死了被下地獄。
1945年5月31日那天(後稱台北大空襲)中午時分,才剛拉警報,我們還來不及躲進在廟後的防空洞,銀白閃亮的B-29轟炸機就已經飛臨頭上,接著炸彈呼嘯地飛越我們的頭頂掉在對街,夷平了整條街,死傷枕藉滿目瘡痍。父親那天騎車出外工作,在總督府附近遇到空襲,他躲進廁所才逃過了一命。據說那天炸死了三千多人,受傷和無家可歸者達數萬人。
我們住的地方正好和總督府(今之總統府)成一直線,所有投炸城内官衙機關偏差的炸彈,都掉到我們那一帶。因此我們被政府強迫疏散到人地生疏又偏僻遥遠的彰化、二林鄉下,但是又再遭到各種致命傳染疾病的肆虐,同去的難民病死了很多人。
在地的鄰居小孩阿忠喜歡和我玩,平日早上都會要我幫他扛一桶杏仁茶去菜市場給他父親補貨,他阿爸「紅毛仔」就會賞給我一碗杏仁茶配一根油車粿(油條),那是我記憶中唯一的也是最美味的點心。至今難忘。
因為父親失業,全家陷入飢貧之中,他衹好冒險回台北找工作,母親卻在那時感染了赤痢惡疾,病況非常嚴重又缺乏藥物治療,家裡衹剩下兩個束手無策的稚齡幼童。幸虧好心的「紅毛仔」嬸以土方的草藥相救,竟奇蹟般地得以治癒。還好不久戰爭結束了,不然我們不是病死也可能會餓死在他鄉。「紅毛仔」阿伯終戰後多年,還到台北來看過我們,聽說阿忠的母親已經過世了。幾次僥倖地逃過大難,全家人劫後餘生的喜悅與感恩的心境實在難以言表。
但是台灣人蒙受戰亂的苦雞似乎永無止境。1947年228事件再次給我們帶來惡夢,但是這次不是「阿督仔」的轟炸震撼,而是尖聲爆響的槍聲在頭上此起彼落,讓人聽了魂驚膽喪,而且開槍殺人和抓人的是來自「祖國的國軍」,原來中國來的「國軍」殺起自己的「同胞」是那麼勇敢篤定!所以後來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時,我一點也不感到震驚,反正他們都是勇於殺自已人的「中國軍」。
國民黨政府「平亂」之後,為了要消弭「國軍」搶劫艋舺「金仔昌銀樓」所引起的眾恕,刻意安排在祖師廟對面的小公園裡將那名「國軍」搶犯槍決示眾,以挽回民心。但是我鑽在人縫中偷看到的衹是大樹腳一灘烏黑骯髒的血,其他什麼也沒看到。這樣也好,免得以後我會因此常做悪夢。
然而殘酷的戰爭景象已經在我幼小的心靈裡刻劃下無法磨滅的傷痕。後來每當我侃侃而談四、五歲時的死裡逃生故事和228身歷其境的往事,聽者多會驚嘆我怎麼還會記得那麼久遠年代的細節。我深以為人一定要記得苦難,才會珍惜幸運的可貴。
〈無根漂萍的半山仔〉
我是個「半山仔」。家父出生於1893年滿清時代,福建、惠安、煙山的一個濱海村莊,年幼時父母就雙亡,他是由嬸婆撫養長大。由於故鄉的宗祠和族譜已經遭土匪燒毀,因此我們家族從父親以上就無根可尋。我和兒子對於我們無據可考的家世都深感遺憾!這是亂世裡小民遭殃的無妄之災。
家父18歲時從廈門隻身東渡台灣,尋找唯一的手足兄長,但是游手好閒的哥哥令他很失望。他聰敏勤勞又遇到貴人,獲得傳授調製優質干漆註2的技術和學得一手漆器施工的精湛技藝,其漆器的作品頗受懂得欣賞此道的日人賞識。戰後其作品還曾經得過台灣省建設廰舉辦「台灣第一屆工藝展」的最佳作品獎,在界業頗受敬重。人們尊稱他「紅九師」(父親名紅九)。(註2:一種由漆樹上採集的樹汁調製成的天然油漆,具有高亮度、高氣密性和防潮耐熱的特性。在歐、亞洲被廣泛用於高級傢俱、棺木、供桌、神器、藝術和工藝品的塗料。)
〈家教嚴格,父母以身作則〉
我家的人丁單薄,家父到47歲時才老來得子,我衹有一位大我四歲的姐姐。照理說,我這個單傳的獨子應該倍受嬌縱,可是父母對我卻管教甚嚴,一切行為舉止都必需循規蹈矩。母親常以「玉不琢,不成器」的古訓來教誨我們姐弟,因此從小就被磨成中規中矩的品學兼優學生。
母親管教雖嚴,但不常打罵孩子,祇在我犯了大錯必須處罰時,才將所有犯過的大小錯,新舊帳一併清算。這招教訓的效果奇佳,因為我搞不清楚老媽何時給我記了「帳」和到底累積了多少「罪」?因此必須隨時注意謹言慎行。家父則是恩威並重,嚴肅但不輕易動怒,零用錢都是他給的,也從未動手打過我們。
我對父母的嚴厲管教至今仍然感激在心。記得小時候,每天晚飯後老爸就坐在我的對面,一邊監督我寫十幾頁的毛筆字,一邊讀他的報紙(我一直很納悶,家父從未上過一天學堂,卻會讀報記帳)。後來我在工程設計圖說上寫的字還可以見得了人,純係老爸當年所逼出來的。
家母是街坊公認有潔癖的主婦,每年清潔比賽的「最清潔」紅色貼紙非我家莫屬。我家的水泥「戶碇」(台語,門檻),都被老母刷洗得露出裡面的紅磚,而且磚塊又被刷成像剛烤出爐的歐式麵包,膨皮又光滑。她煮料理的功夫也遠近馳名,鄰居娶媳婦時還幫人家辦了廿幾桌酒席,比餐館的菜肴毫不遜色。她出門上街,無論是赴宴、看戲或買菜,必定梳洗打扮得乾乾淨淨,外表永遠保持光鮮亮麗,對家人的要求也毫無例外。她常說「家裡吃好吃歹,人家看不到,但是出門衣衫不整蓬頭垢面,就會遭人瞧不起」。祇是我和親友們卻憂心忡忡,家裡有一位這樣的婆婆,我將來娶得到老婆的機會就可能非常渺茫。
〈殖民地的賤民〉
由於家父是日本統治台灣時期才從唐山來到台灣,籍貫一直都是福建省惠安縣,我是到小學一年級領奬狀時,才發現原來我的籍貫和別人不同。後來我又記得戰時我家領到的配給品份量和種類都比別人少,我記憶最深的是有小孩的人家可以配給到Ame-ta-ma(アメタマ日本糖球),唯獨我家沒有配到。那糖球是戰時小孩唯一吃得到的零食糖果,別人都有糖球吃唯獨我沒有,哪有多麼傷心啊。有時鄰居可憐我們姐弟,會送一點給我們,我們就如獲至寶的留著慢慢享受。
原來那時候我們是比「四等公民」的台灣人還不如。長大後,我查問當時台灣人如何被區分,得出的結論是;「一等公民」是血統純正的日本人(就像連戰那種Pure Chinese的「高級外省人」)。「二等公民」是改姓日本姓和日本名字的台灣人,全家人講的是日本話,完全「皇民化」,享受幾乎和日本人一樣的待遇,衹差身上沒有半滴日本人的血而已。「三等公民」是還姓著自己原來的漢字姓氏,但是取日本名字的台灣人,不一定都講日本話,待遇則比皇民化的台灣人差一截。最下等的是什麼都没改,仍然保留著漢字姓名的「四等公民」。像我們這種連籍貫都還是原籍的「支那人」(shi-na-zin),可能是被歸類為第五等的「賤民」或什麼東西都不是的「清國奴」(chan-ko-ro)。
〈改籍貫〉
像我這種父親是「唐山人」,娶台灣某所生的「半山仔」,不知算是什麼碗糕?雖然我不瞭解父親在228事件後為何將全家人的籍貫改為台灣,但是我可以從記憶裡發現他不時訐譙國民黨政府貪腐,和瞧不起當時接收台灣的那些軍紀蕩然無存的陳儀部隊的不滿情緒,猜想必定與這些因素有關連。
家姐到適婚年齡時,因為開始有人追求,家父就先訂下了「絕對不可以嫁外省人」的鐵律,可是卻引來母親的偷笑和「他自己不是外省人嗎?」的反應。
父親當時的觀念我現在可以理解,他一定是認為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幾十年了,他當然就是台灣人。他無法接受那些持統治者姿態的外省人。他曾說過日本人對待台灣人也沒有那麼殘忍(指228事件的殺戮)。我老爸並不是人格分裂。
不是讀書人的父親,有他自己的一套人生觀。我一直認為他懷有功夫,從小我就常看到他幫人家推拿輕微的扭、挫傷,和幫人勸架息事時的矯健身手,以及街坊盡知他是抓賊的高手,我大概從這些觀察看出一些端倪。我記得至少有兩、三次他是晚上在樓仔厝的屋頂上將小偷追捕到手,再交給警察或刑事(偵探)法辦。我很喜愛柔道運動,也常去道場看人家練習,但是父親卻不充許我學。他認為年輕人血氣方剛,別人若是得知你有功夫,就會來挑釁,結果為了自衛可能傷人或被人所傷。我祇見他與人為善,從末看過他和人爭吵。
〈懷念的老街與眾生相〉
終戰後,我們搬回舊居的後街(今之隆昌街,鄰近西門町),住進一間日本人戰敗返國所留下來的日式木屋(後來父親依法向國有財產局購得產權)。街道雖然狹窄,人情卻很豊厚。我們那條街上各色人等俱全;有晚上打扮得花枝招展去上班的應召女郎和酒女,也有體面的法院書記官、高階公務員和樸實無華的的上班族,更有白天踏三輪車,晚上在酒家走唱賺錢養家,平日對鄰居和氣有禮的大尾角頭兄弟。
記得住在我家對面的邱先生,在228事件過後不久的一個晚上,突然被一群軍警挀走,從此就在人間蒸發,沒有再回家。當時邱太太孤單、焦急、無助又走投無路,兩個失去父親的孩子變得落落寡歡,與鄰居小孩格格不入的情景,深植在我幼小的腦海,至今難忘。最終邱太太和孩子搬離我們社區,從此失去音訊下落不明。這是我親眼目睹228受害者家庭的悲慘往事。
我們老街的孩子們相當爭氣,短短一兩百公尺的街上,就有七、八個功課優異就讀建中、成功和北一女的男女學生,也有兩、三位讀台大法律和其他讀成大化工、台中農學院(今之台北大學的前身)及台北工專的學長。其中讀台大的學長,一位是豬肉販的兒子,另一位則是在廟前賣紅豆、花生湯阿伯的老二兒子。社區的成員當然也良莠不齊,街坊不乏吃喝玩賭耍流氓的少年家仔,可是有位大哥住在那裡,至少他們不敢太過份放肆。
我也看過不少角頭火拚打打殺殺的血腥場面,更親眼目睹管區警察與電信局人員等牛鬼蛇神,明目張膽保護與掩護非法,並在應召站打情罵俏「摸蛤仔兼洗褲」(收紅包又吃豆腐)的無恥醜陋行徑。去廟前看打拳頭賣膏藥、捏麵人、吹糖葫蘆和觀賞布袋戲及看無聲電影是我少年時代課後飯餘的最佳餘興節目。
這個多釆多姿的社區我一直住到結婚之前才不捨地搬離那裡。我就是在這種複雜的環境裡成長。它不衹助長我思想早熟和確立自己的價值觀,也幫我看清楚社會的百態、病態與醜陋的面目,以及人性的冷暖與善惡的一面。對於我以後處世待人助益不少。
〈家變逼上苦學路〉
初中即將畢業時,父親撒手西歸,我遭逢人生最大的衝擊。他臥病一、兩年我們已經家徒四壁,去世之後家計更陷入困境。上無長輩給予援手,父親的生意又被合夥人無情地接收。幸虧他身後還留下那間簡陋的木屋,可供我們母子遮風擋雨,否則後果更不堪設想。此時才領略到人情的冷暖,我們孤子寡母祇得堅強的相依為命,在絕境中自力更生。
繼續正常的求學已是毫無可能,記得我的建中嚴師譚家培老師在得知我父喪的消息時,在課堂上當眾對我說了一句永遠難忘的話:「李健兒啊(Ken-ji是我原來取的「假」日文名字,父親說哪既是漢文也是日文,可以避免報戶口被找麻煩),以後你的破書包難背囉!」果真從此以後我就走上艱苦的工讀苦學的崎嶇求學路,也導致我立誓將來無論多麼困難,一定不再讓自己的孩子重蹈我艱辛求學的覆轍,衹要孩子能力所能及,我們一定要提供給他們最佳的教育機會。
〈因缘際會小工變老闆〉
我很幸運得到同學父親的幫助,介紹進入台電公司。歷經十年的努力奮鬥,從卑微低層的臨時短工(額外的短期僱用人員),在一邊讀書一邊上班的工讀環境下,通過層層的升等考試與考核,終於爬至「電機工程師」的職位。也許它對有文憑的人就可以輕而易舉達到,但是對我卻意義非凡,那是累積數年的忍飢挨凍、勤學苦讀和艱辛奮鬥才達到目標。
不過,我也認清自己沒有高學歷與有力的人事背景,而且不善於交際和逢迎討好上級,僅憑著戆直的幹勁在國營機構是毫無前途可言。況且捧著「鐵飯碗」一直幹到退休,也並非我的人生願景。雖然年年的考績屢得甲等,甚至有一年還意外獲得呈報經濟部的「特優」殊榮。可是除了多拿一個月薪水的獎金之外,對我實在毫無任何實質的意義。更未料到這是「塞翁得馬」之禍!多年之後全家移民,在僑委會申辦僑居護照,審核時竟因為這份「殊榮」被擋下,差一點出不了國。原因是我被列管為出境受限制的「國防技術人材」,天啊!曾幾何時我變得對「中華民國」有那麼重要啦?早知我就應該留下來升官發財。最後還是替我辦理護照的旅行社朋友去想辦法為我解套才出得了國。
1960年代,台灣的經濟開始起飛,「十大建設」和不斷引進外資,到處大興土木,對於硬體建設的設計和施工人才需求孔急,民間事業大量聘請有真才實力的工程人員。此時,適逢有人要高薪徵聘我去民間的工程設計事務所,主持設計外資建廠和公、民營大項建設的電氣、電力工程。
當時我正值家中老母年邁多病,新婚妻子又身懷六甲,家裡的醫療和生活開銷與日俱增。雖然我們夫婦都在上班,我晚上還在建築師事務所兼差做電氣工程設計,但是微薄的薪資和兼差收入還是經常抓襟見肘入不敷出,家庭的財務日漸陷入困境。鑒於家庭收入的現實需求和考量自己未來的前途,認為這可能是我應該慎重考慮變換跑道的時機了。衡量分析得失的結果,就毅然決定辭掉「鐵飯碗」,踏進民間機構去冒險打拚。
經過幾年的努力和完成多件指標性的重要設計,頗獲一些歐、美、日外資大公司和本土建築師事務所的賞識與信任,工程委託設計的案件應接不暇。又受邀赴日本觀摩見學超高層建築設備的設計和施工新法,並且有幸參訪各大電機製造廠和大阪的世博會,眼界得以大開而且工程技術智識也增益良多。
返台後不久,和朋友共同合作創業,我負責主持專門設計兼施工的工程公司,訂立不參與競標和不做公家工程的經營原則(由於親眼目睹過太多弊端),和絕不以送回扣或請喝花酒來爭取生意。衹承接信任我們技術的民間事業、建築師和外商所推介委託的設計和施工案件,戰戰競競以良心和敬業的態度經營業務。經過數年埋頭苦幹,事業漸有小成,家庭生活也獲得許多改善。
〈煩惱的開端〉
三個小孩(二女一男)陸續邁入學齡時期,由於無法認同我們送去「試讀」的一些私立名校的貴族辦學方式,遂將兩個女兒送至教會辦的幼稚園。接著入讀公立小學,她們的功課都很好,也都當了班長,深受老師們的喜愛。她們有空參加校外的音樂班、合唱團、學鋼琴、繪畫和溜冰,非常快樂。唯一的問題是我不讓她們參加課外補習,老師不解,我也不便去解釋說明。因為我無法告訴老師,我從小就痛恨補習。我要我的孩子們有更多時間自由學習、遊戱和活動,看更多有趣的課外讀物,有她們自己快樂的童年。老么兒子則被送進實驗幼稚班,不必學習八股的勹夊冂匸注音、寫字和認字,上課時可以自由走動,選看自己喜歡的圖書和玩自己喜愛的玩具,唱遊之外就是種花除草和澆水照顧花木。而且他在班上有十個女朋友,快樂無比!
可是隨著孩子們逐漸長大,老婆的憂慮也逐漸跟著升級。她終於忍不住質問我,這樣不讓孩子補習,不給他們諗私立的「好學校」,這種「野放的教育方式」繼續下去,將來若是無法進入「名校」的初、高中,考不上「好大學」,要怎麼辦?我一時無法回答這一連串天大地大的問題,也不敢理直氣壯以「有為者亦若是」的豪言壯語來反駁她,因為萬一孩子們不爭氣,哪我的責任可就重大了,到時候我一定被叮得滿頭都是庖,並且罪無可赦。
孩子來到這個世界並非他們自己的選擇,我們既然把他們生下來,就有責任將他們撫養教育「成人」,我們必須給他們能力所能及的最佳安排。天地之間總有容得下我們親子的理想生存空間吧?!我遂開始思考我們和孩子將來何去何從的問題?這是煩惱的開端。
由於當時正值台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化劇烈的時期,人們的價值觀與社會風氣急驟改變,對於自己土生土長的鄉土我竟然感到陌生又迷惑不解。我突發奇想,要和至交的好友來一次攜眷出國觀光旅遊,一則是要疏解壓力,再則想要一窺外面的世界,尤其是響往已久的北美地區。
西遊記
〈巧遇與起心動念申辦移民〉
1978年,我們夫婦狠心放下工作和生意,從夏威夷開始,再進入美國西部各地。足跡遍及聖地牙哥、洛杉磯、拉斯維加斯、大峽谷、舊金山,最後抵達西北邊疆的西雅圖。計劃在那裡申請加拿大簽證,再進入溫哥華。
在西雅圖的加拿大領事館内申請簽證時,巧遇一對張姓夫婦和一位袁先生,不期的相遇卻引起我們思考是否移民美國的另一個煩惱。
移民美國?當時這個議題對我們而言,猶如天方夜譚,壓根兒就從未有過那個念頭。可是由於那些陌生人的意外推薦而與移民律師見面約談,跟著深入的咨詢結果,竟導致後來起心動念辦理移民的一連串意外發展,這實在是我們當初出遊散心所始料未及的。
〈面對人生重大的決擇〉
遊美假期結束,帶回美麗難忘的回憶,同時也裝了滿腦袋的煩惱而歸。美西之旅,一路由南往北觀光,也到過當時華人移民聚居最多和最響往的洛杉磯和舊金山。雖然這些城市繁榮熱鬧,生活方便,語言溝通也容易,但是環境複雜、治安不佳的大都會生活我們並不喜歡。反而最後扺達的西雅圖,民風純樸友善,物產豊富氣候宜人又環境優雅,是很適宜居住和養育小孩的環境,我們對那裡的印象深刻又喜愛。
經過慎重的全盤衡量評估的結果,認為故鄉台灣雖然是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根基,有無法割捨的情懷與家庭和社會關係。但是考慮台灣的社會、經濟、居住、環境、政治、治安和教育等問題日益複雜,對於將來的遠景及孩子受教育的前途,無法樂觀期待。最後決定趁我們尚年富力壯之際,要出外打拚就必須趁早。而且老母已經去世多年,沒有家累需要照顧的顧慮,故若想離開故鄉,也沒有太多牽腸掛肚不易捨棄的因素。唯一較難以處理的是事業要如何結束,和對親朋好友如何說明交代,尤其是內人娘家的長輩。
〈辦理簽證與台美斷交〉
以我們不是來美留學和在美没有親戚關係的身份,照理辦移民是不容易的。可是我們申辦的過程卻超乎尋常的順利快速。可是問題卻出在我們申辦時台美關係是正常的,等我們取得美國移民局的核准文件,台美卻才剛斷交,雙方一切外交事務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台灣的美國大使館已經撤退,在台灣沒有領事館。規範台美非官方外交事務的「台灣關係法」還是後來國會倉促催生出來的外交「怪胎」產物。我拿著核准文件無法回台灣簽證,不知何去何從,首次真正體會到「國際孤兒」的台灣,處境竟是這般可悲。
最終,律師建議去最近的溫哥華美國領事館試試看。我們抱著半信半疑的心情去到溫哥華的美國領事館,辦理過程卻異常順利。
我們在美國辦理移民的過程都出奇的順利,好像山姆叔叔一直張開著雙臂在歡迎我們。後來申請綠卡、歸化美籍也都一帆風順,覺得移民來美似乎在冥冥之中已有安排。
深耕他鄉如故鄉
〈新移民的辛酸〉
每個移民美國的人都有各種不同的原因,有人是年輕時負笈海外,畢業後找到工作,然後結婚生子,就順理成章的在這裡生根了。有人因為依親或專業就職而移民。也有像我這種當年為了孩子的教育,憑著一時的衝動,放棄家鄉的一切,攜家帶眷來到舉目無親又人生地不熟的異鄉。這一待,就是三十幾年。
剛登陸新大陸時,一切都必須從零開始。我僅憑著自己在台灣與外商多年打交道的一點點粗淺英語文基礎,和不容許回頭的形勢所逼,祇能帶領著全家人勇往直前,移民的辛酸經歷確實一言難盡。
我們抵達移民目的地西雅圖時,正值黒、白學生school desegregation的student busing政策在各地嚴厲執行的時期。但是剛登陸的我們既不明瞭其基本的法理意涵,更不知如何配合哪種亂七八糟的「不便民教育大戲碼」(後來證明是政治把戲的鬧劇一場,至1980s就無法繼續演下去。因為虛偽的假面具被揭露,一群大力主張推行支持Busing政策的著名國會議員、聯邦法官和媒體作家,都將自己的孩子送去讀私立的學校),尤其我們一句英語也不懂的孩子們實在無需遭受這種折磨。
為了避開那種拿小孩子當白老鼠來折騰的都會學區(如:西雅圖學區),我們大膽搬進多數為猶太人與白人家庭的市郊小學區。也幸虧得到剛認識的美國朋友幫助,幫我們找到屋主自售的物美價廉房子,讓我們有個棲身之所和孩子們可以安心求學的學校可讀。
連ABC都不認識的三個小孩,就直接被送進一、三、五年級就讀,大人和小孩的辛苦不在話下。一年之後,ESL班的老師就宣告不再收留他們,他們已經没有語言的問題了,他們甚至開始被送進advanced classes。多年之後,當我和妻子兩次在孩子的高中畢業典禮時,以valedictorian的家長身份被請起立接受來賓的致意時,因為觸動了我們一路走來的辛酸舊憶,百感交集之下幾乎當場失態落淚。
〈歹竹出好筍〉
孩子們沒有讓我們失望,無論在功課或課外活動各方面都表現優異。有時半夜起床,看到孩子的房間裡電燈還亮著,原來他們還在挑燈夜戰努力用功,祇好叮囑早點休息注意自己的身體。申請大學時我們從未參與任何意見,我們更沒有時間和金錢陪他們去看學校,野放的教導方式已經讓他們練就了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和要怎樣做才能夠達到目標。
老大女兒接到外州學校的接受函,因為我們還在為生活掙扎打拚,她自動退而求其次,進入華州最好公立大學。畢業後做事幾年累積了經驗並賺取學費,再進入CMU研讀深造她的IMBA學位。現在芝加哥擔任IT Product manager。
老二女兒被長春藤幾個學校接受時,我還在地球的另一端為生意出差打拚,無從幫她做任何決定。她自己買了一張機票飛去波士頓找她的學姐,在哈佛的女生宿舍打地舖睡了幾天,看她喜不喜歡那個學校。就從此與哈佛大學結了十年的不解緣,博士畢業時她是抱著一個和牽著一個小孩,上台去領文憑的唯一女生。她從小就知道自己要走什麼樣的路,該怎麼走。從西雅圖到波士頓,再到英國牛津一年取得碩士並找到對象。畢業後在歐洲工作一年,就在牛津校園的教堂和讀完PhD的德裔男友結婚,然後回哈佛俢PhD。他們在紐約做事定居十幾年,育有二男一女。
長春藤的大學大多既勢利又世襲,學生走路也真的有風,連哈佛廣場的流浪漢也與眾不同,出手就可以下得一盤好棋。頂尖的精英都在大學部,但是含著金湯匙來出世的學生卻很多。女兒的同學曾經這樣問她,「你爸爸是教授或醫生?」她的回答是我爸爸祇是識字而已,差一點害她們跌破了眼鏡。哈佛是很幸運才招到她。
老么兒子從小喜愛運動,七歲開始踢足球就成了他的事業。從Select team U13打到U19,南爭北戰還越界打到Canada、Mexico。申請大學時許多校隊教練爭相勸誘他去讀,最後他選了史丹佛並立即去學校參加選拔,整個暑假的吃住就靠學校供應。可惜祇打一年校隊,就以功課為重不再繼續效力。加大柏克萊給他Full ride讀碩士,畢業後他卻跑去密西根大學讀法律。法學院第三年開學時,人家都開始在忙著找工作,他已經有暑假去實習的那家Law firm聘書在手上。
從史大校園延續到芝加哥,歷經九年的愛情長跑,兒子終於和印度裔的學妹結為連理,生了兩個女兒。夫婦各自在芝加哥的法、醫領域努力奮鬥。
〈犧牲享受 享受犧牲〉
來美含辛茹苦,雖謂是為了後代,其實也考驗了自己的生存能力。如今孩子們都已進入中年,我們所有的努力成果卻都展現在每根蒼蒼的白髮。雖然過去的歲月犧牲了不少「享受」,但目前也享受了「犧牲」,人生本就得失難辨。參透了,豈不就是時也,運也,命也?
昔日登陸時的一家五口小家庭,己组成了12個成員的「小小聯合國」,孫兒們漢、英、德、印、西語(nanny的語言)五音雜陳,可惜唯獨台語鄉音快成為絕響,衹剩兩佬在為維護母語苦撐,情何以堪。
〈歷經國難 共體時艱〉
2001年九月上旬,女兒懷第一胎即將分娩,為迎接第一個第三代來臨,我們趕赴紐約曼哈頓陪女兒待產。
9/11清晨六點,我們的第一個孫兒在NYU醫院順利誕生,母子均安,新科的阿公、阿嬤滿心喜悦。我們八點多拖著疲累的身體回到女兒的家想小睡休息一下,不料九點鐘住在Flushing的外甥來電告知好像世貿中心被飛機撞了,交通管制他無法進城上班。我們打開電視看新聞,正在播報North towel被飛機撞上燃燒中時,現場銀幕上又目睹第二架飛機撞上South towel。這時大家才驚覺不是意外事件,是蓄意的恐怖攻擊在進行中。接下來全國天翻地覆的壞消息頻傳,五角大廈也被撞,更多民航機被挾持。手機通訉全部失聯,我們無法和女兒、女婿連絡。還好女婿那天沒去華爾街上班,否則會急死人。
世貿的雙塔延燒兩小時後陸續崩塌,我們含淚眼看著螢幕上警民和消防員奔跑逃命,滿街煙塵迷漫的畫面,宛如世界末日降臨。
往後一週的曼哈頓如同孤島,除了軍警車輛和少數的貨運補給卡車可以進城之外,其他人車衹准出不准進。兩天後我和女婿去接女兒母子出院,NYU醫院收容了眾多傷患,門禁戒備森嚴,到處路障和軍警巡邏,捐血的民眾也大排長龍。交通管制祇有軍警消防車優先,平日卅分鐘的車程,我們足足花了四個小時才回到家。民眾沒有人抱怨或不滿。
紐約這個看似冷漠混雜又不太安全的大都會,在國難當頭的時機卻表現得可圈可點。民眾生活一切如常,購買物資時祇取平日正常所需的份量,没有人搶購屯積。商家的供應雖然貨源有限,但不會居奇抬價。大家平和共度時艱,充分表現泱泱大國國民的素養與鎮定自信,New Yorker實在令人刮目相看,也肅然起敬。
尤其那段期間據報犯罪率奇低,眼見執法人員死傷那麼慘重,又要忙於執行維護安全的警戒,連不法份子都不好意思作奸犯科或趁火打劫了。許多死傷慘重的消防隊門前,擺滿民眾點燃的祈福蠟燭,和堆積如山的鮮花及慰問卡片,這樣有愛心有良知的社會,竟受到無情的恐怖攻擊,真會人神共憤。美國歷史這悲慘的一頁,我們也親身經歷其間。
有夢最美 築夢踏實
我們夫婦在美各自創業的過程中雖然都很艱辛,也備嚐了各種逆境的考驗,但是都順利渡過難關,並且獲致成就,全家人得以安居樂業。這個國家和社會更提供給我們第二代優質的教育和平等就業的機會,孩子們承蒙諸多公私立學校教導並且慨贈優渥的獎、助學金,幫他們順利完成各項學位,畢業之後也都謀得滿意的工作。非常欣慰他們已能夠回饋,使那良善的基礎得以延續,幫助更多其他有需要的人。
我們在這自由民主的美麗異鄉與其他先來後到的移民共同埋首深耕,一起追尋美國夢。有夢最美,祇要築夢踏實,秉持著建國先賢的理想與智慧傳承,終會達成。 (6-9-2015於芝加哥)
摘自 芝加哥台美人故事集 (Taiwanese American Journey to the West/Chicago/Volume I)/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