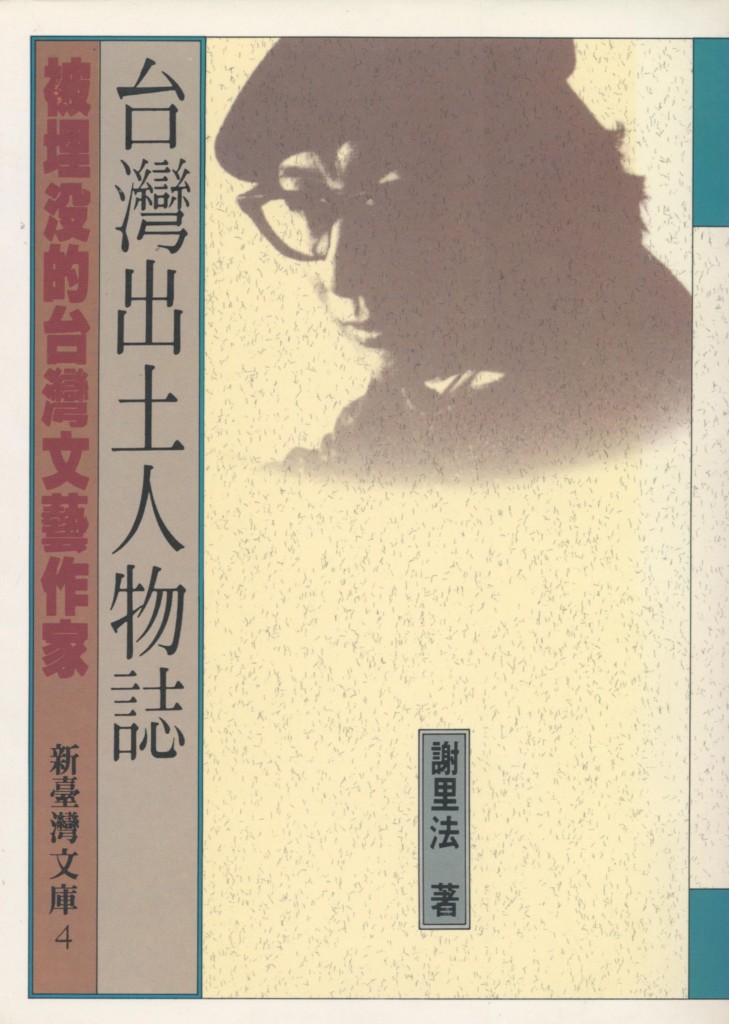台灣出土人物誌
作者 謝里法
水牛物語 –
「臺灣出土人物誌」自序 謝里法
台灣的美術家向來踩着矇矓的史頁完成其一生的創作。直到近兩年,方才以原來的面貌而呈現在一部較完整的臺灣美術史上。因此,收集在本書裏的八位藝術家,至少有三十年時間是被臺灣的畫壇所遺忘了的。
就拿我個人經驗來說,我勿寧說那是在一個沒有美術家的時代裏暗自摸索,而後尋找出他們的存在。
小時候,在臺北太平國民學校讀書,經常逃課跑到新公園博物舘的閱覽室裏看閒書。有一回 ,在兒童刊物上偶然發現一張圖片,是三個裸體小男孩伴着五隻水牛的浮雕,作者名叫黄土水, 並註明這件作品存放在中山堂後廳的一面牆上。第二天,我放學後跑到中山堂去,果然在後廳從二樓走上三樓的中間梯口牆上看到了這幅巨大的浮雕。那時的我雖不懂美術,但還是瀏覽了好久好久方才離去。下樓時,在右側另一道梯口又看到一幅畫,畫着一隻十分華麗的大帆船,描繪的工夫異常細緻,不知作者是誰。那天以後,每過中山堂必進去探望一眼再走,這是我與臺灣美術最早的一次接觸,印象很是深刻。
年紀稍長,每年一度跑博物館看「省展」,又到福星國民學校看「臺陽展」,這才得見全島各地臺灣美術家的作品。我最喜歡的是藍蔭鼎的水彩畫,聽說他到過美國,是美國什麼水彩畫會的會員,對他又更加崇拜起來。
進大學美術系以後,認識了系裏的老師廖繼春、林玉山、李澤藩,以及校外的顏水龍、楊三郞、張義雄等畫家,對藍蔭鼎已開始不感興趣。但最關心的還是西方的藝術世界,一意只想學習巴黎新的畫派,逐漸對島內畫家的創作情形無心顧及,從此便沒有機會再進一步了解臺灣晝壇的事。
一直到學校畢業十幾年後,流放他鄕的心開始思歸,囘想起自己對臺灣美術在過去這麼長一段日子的空白,這種自覺,不但令人吃驚,而且是惶恐,是心寒。
猛然囘首時見到的這片空白,它不只意味了我個人多年的自外與無知,也意味了臺灣文藝史料的荒蕪和臺灣文藝工作者所受的漠視。對此,若有人借着外族殖民的特殊境遇,或未開放的政治環境而辯解,也都不足以作爲這一代人自卸職責的理由,更不足以使本來空白了的史頁塡造幻影,藉以自慰。
我想起了中山堂牆上的水牛浮雕,記憶中它該是擺進世界上任何美術館都不遜色的隹作,也想起了那幅富麗堂皇的大帆船,以及他們同時代其他美術家的作品,是否安然無恙,在與島內畫友的通信中,我開始提出詢問。正當衆人對海外藝術思潮抱熱切嚮往的當時,我囘頭來問起早已遺忘了的五十年前畫壇舊事,對方無不因我這行徑感到費解,也着實給他們帶來莫大困擾,他們和我一樣對臺灣美術的過去所知無幾呀!
初時我僅以獲得的片斷傳聞聊以自慰。然不完全的史料反將歷史顯得更離奇,甚至把剛去不遠的史實帶入近乎神話的世界。
儘管傳言中的史頁撲朔迷離,但長年累積的斷簡殘篇,仍然被我接駁串成了 一段五十年美術活動的斷代史。就這樣我以四年時間寫成一部十五萬言的「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島內友人無不爲此而驚奇。事實上,我不過只將荒廢了的修補,使之返囘原形,並沒有新的發現,說正確點,我這樣作只是爲了塡補自己內心的空白。
該書出版後,讀過的朋友見面時免不了問一句:這許多資料是怎麼得來的?然更可貴的還是 ,各方給予的評語,有提供補充資料者;有代爲指出與史實不符者.,有現身說法寫來親身經歷者 。雖然受到批評多於褒揚,我仍然以一本書而得來這許多囘響感到欣慰。
這當中最最令我興奮的,莫過於激勵了臺北「雄獅美術」月刊推出臺灣先行代美術家專輯的 構想,以及因之得以與早年遠赴大陸及今了無訊息的幾位畫家後代有了聯繫。收錄在這本書的八篇文章,就是在這兩種因緣下寫成的,不但又挖掘出幾位向不爲人知的臺灣美術家,也塡補了「 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的不足。
「雄獅美術」的「臺灣美術家專輯」始自一九七九年三月,每月推出一位,共有顔水龍、黄土水、林玉山、洪瑞麟、郭雪湖、陳澄波、陳夏雨、李石樵、藍蔭鼎、陳進、李澤藩、李梅樹、劉啓祥、楊-郞、林之助、廖繼春、郭柏川、張萬傳、沈耀初等十九位畫家和彫刻家,約歷時兩年才結束。其中徐了藍蔭鼎、廖繼春、楊三郞、李石樵、林玉山等,因活動較多,知名度較廣以外,其餘的视已很少人知道他們的存在。這十九位美術家分別由十個人負責執筆,我因資料較豐 ,又是專輯的推動者,所以單獨坑責了黃土水、郭雪湖、陳澄波和廖繼春等四人。
這本「台灣出土人物誌」僅收錄「臺灣美術家專輯」裏的黄土水、郭雪湖和陳澄波三位美術家。由於黃土水和陳澄波二人逝世已三十年以上,一時史料難尋,能在圖書館查獲的隻字片紙, 用之以述及一個藝術家的生涯,必然過於簡陋。爲此我輾轉委託在臺友人,尋找散居各地黄、陳 二氏家族,取得聯絡後,得到他們的諒解,接受筆訪,並提供一份十分完備袖生平年表和生前遺照。同一時候,「雄獅」方面也熱心奔走,尋訪收藏作品的富戶,拍攝作品照供我參考。有了這些之後,兩位隱沒三十多年的藝術家的輪廓便逐漸呈現在我的腦際。
當年初見黄土水浮彫時,雖由衷喜愛過,等全面看了他一生創作之後,幾乎已認定他具備成爲世界一流美術家的各種條件。設使不是三十六歲便逝世,其藝術成就晉昇國際藝壇是可以預期的。尤其可惜的是,因他的早逝而未能將這優秀的彫刻傳統在臺灣奠立,又由於遺作深藏在富戶人家,鮮爲人知,以致藝術的影響不得施展,這是臺灣美術史上的一大憾事。
黃土水一文完成後命名「臺灣近代彫刻的先驅者」,發表於一九七九年四月號的「雄獅」, 因黄土水去世於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八〇年就是五十週年,便乘機鼓吹收藏黄土水作品之人士合 力皋辦r紀念黄氏逝世五十週年遺作展」。然由於我人不在島內,且藏家也各有顧慮,致使遺作展未能如願,期待中黄土水彫刻的復興終於流產。
與黄土水同年出世的陳澄波,留日時間晚黄氏將近九年,因此當他學生時代,黄土水已在東京嶄露頭角了,這使他愈加奮發,於在學期間作品便已入選「帝展」,消息曾在臺轟動一時。學業結束後,他轉赴上海敎學,一度活躍於上海畫壇。一九三四年囘臺籌組「臺陽美術協會」,與在臺畫家合力倡導美術運動。從此定居臺灣,直到二二八事變發生,他代表嘉義民衆與國民黨軍除交涉,終於在火車站廣場被槍殺示衆。有了這樣的結局,他盼名字也隨之從臺灣畫史消失,三十多年來幾沒有人敢在文章裏提起他。爲此「雄獅」推出專輯時頗爲小心,我的文章也遭雜誌社愼重刪改。後來編者來信表示,其所以這樣作是依陳氏的大兒子陳重光先生的意思,希望我能諒解。其實對受難者家屬的苦衷,這些年來,我已相當可以理解的了。
前幾年,從畫界前輩聽來一段令人尋味的小故事:陳澄波本是個「稚氣滿滿」的藝術家,「光復」初期,他基於愛祖國愛同胞的心,在畫家之間勉勵同儕講國語。不久事變發生,他被槍殺了,畫友們反而引他的例子互相警惕:「澄波仙就是講國語講死的。什麼都可以學,就是這點不能學!」講國語也會講死人,就只有這時代才有呀!
有關郭雪湖的文章,我寫得較長,大約四萬字。寫到他四十歲時,覺得已足以代表他的一生,就沒再寫下去。
郭老先生晚年定居美國西海岸,因而撰寫期間有機會前往採訪,過後又以書信請敎,一年之間收到的信長達五十餘頁。他的文筆順暢,思維淸晰,不僅把自己這一生事蹟寫得詳盡,且將畫家間的交遊情形作深入描述。以致文章發表後,讀者中不少人以爲我是郭先生同輩的人。
這篇文章裏,筆者刻意提出「臺灣畫派」這名詞。因二十世紀初巴黎曾以「巴黎畫派」( Ecole de Paris)自稱,看了郭雪湖早期作品,心裏不期然想起了「臺灣畫派」。在當時摹仂古人畫法的保守晝壇,他睜開藝術家的眼睛觀察生活中的臺灣景物,將感受納入畫幅。他的創作源自臺灣的眞實經驗,於臺灣近代美術發展的過程中,可謂畫出臺灣精神的第一人。這樣的作品應該有很大的將來性,可惜一場戰爭帶來的變動,文化價値遭到無謂的蒙蔽,畫家創作從此陷於朦朧境地,郭雪湖隨之從臺灣畫壇消失。等再淸醒時已經三十年過去了。
至於與滯留中國大陸的臺灣美術家家屬聯繫之事,約始於一九七九年底,那時中共剛開放與外地自由通信,而我在這時機找出江文也、范倬造、劉錦堂和張秋海等四位,套句臺灣俗語,眞可拿「看一個影,生一個子」來形容。因爲我那時只要能打聽到一點點消息,不管確實與否,就寫信去査詢,不厭其煩繞着大圈,走了不知多少寃枉路,終能在三、四年之間將這幾位藝術家尋找出來。
首先與我通信的是江文也夫人吳韻眞女士,詳細經過在本書最後一篇「出土的話——斷層下的老藤」裏將有交代。但出乎意外的是,吳女士對旅居北平的畫家,除張秋海外其餘的居然一個也不認得,甚至名字也未曾聽過。看來在北平的臺灣人之間,彼此交往並不勤甚至懷有戒心,這也是我尋人所以困難的原因。
當年江文也離開東京前往北平,正如他在「聖詠作曲集」後頁所寫:「中國音樂好像是一片失去了的大陸,正在等着我們去探險。」探險的結果如今已揭嘵:江文也終於在這一次–也是此生唯有的一次探險中失踪了。且又發現失踪的探險者不只他一人,除了本書裏寫的幾位,還有更多的人待我們去挖掘。中國竟成了探險家的墳墓!不久前,中國一再把出土文物運到世界各地展覽,以宣揚其文化歷史,然而創造這文物的人物,却從來沒有人關心過,難道說中國的文化是一羣不受關心的人創造出來的!
書中關於范倬造一文,是透過此間朱曦先生和北平「美術」月刊吳步乃先生協助,才從北平中央美術學院、廣西藝術學院彫刻系畢業生以及范夫人齊女士處獲得文字和圖片資料,又經在臺畫家顏水龍先生過目,證實范倬造乃是到北平後更名的范文龍,才落筆寫成的。范氏到北平不久,卽被派去廣西,對廣西藝術學院創設彫刻系有很大貢獻,在廣西的環境下,能讓一批對彫刻一無所知的靑年學生明白彫刻爲何物,這種從知識上建立的奠基工作,唯有如范倬造經過日本學院嚴格訓練的美術家,才得以勝任。學生們說:「范老師本身就是一尊彫刻!」言中必有道理。
與另一位畫家張秋海聯絡,是經吳韻眞女士介紹的。張老先生是十九世紀末出世的畫家中碩果僅存的一位。早年他在東京專攻油畫,到北平敎學時因故僅擔任工藝美術課程,因而荒廢了油畫創作,以一位美術敎授而終其一生。但當我看過他的部份作品之後,却發現他在西洋畫上的造詣,尤其是學院基礎的功力,確是紮實而又深厚。對此,我只有深深爲他惋惜,設使當年他從故鄕遠走高飛前往的不是中國,而是這世界的其他地方,他的才能有適當環境得以發揮,那麼張秋海肯定不是今天的張秋海。也由於這緣故吧,使他對功名看得十分淡泊,當我在信中問及他的生平時,囘答總是:r這一生已沒有什麼好寫的。」因此這篇文章所用的資料,都是後來通過吳步乃先生向他的學生間接要來的,就是作品圖片也要經由熱心的學生乘他不在時偷偷從家裏拿出去拍來的。沒想到他竟然如此認命,寧可葬身地層而不願出土重見天日!
至於早逝的劉錦堂(王悅之),能夠與他的後代通信是非常偶然的事。有一天,劉錦堂的第三兒子劉藝先生到北平「美術」雜誌社,詢問他父親早年老同事的近況,會見的人正好是吳步乃先生,哭先生剛讀過我寄去的「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略知劉錦堂其人,就這樣把劉藝先生介紹了給我。通信之後,知道劉藝先生也是美專出身,是位知名書法家。雖也寫過文章介紹自己的父歲,總覺得環境限制無法暢所欲言,很希望能借我的筆把他所不能寫的寫出來。信中他一再表示,劉錦堂不論藝術上的才華、社會上辦事的能力,都超過同年紀的徐悲鴻,只因爲是臺灣人的緣故,兩人在中國畫壇的地位竟有天淵之別。他稱謂劉錦堂是「臺灣的蕭邦」,或是「蕭邦式的臺灣藝術家」,「他在中國大陸過着坎坷的藝術生活,受盡了歧視、謾駡和攻擊,始終不改其志,終能在自己的藝術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他認爲從蕭邦的身世便可了解劉錦堂客居北平的心情。凑巧林衡哲先生論江文也的文章裏也以「臺灣的蕭邦」比喩江文也,劉江兩人都是當年在北平的金灣人裏最有成就的藝術家,他們的作品與詩詞流露故土的情懷旣深且濃,說這是藝術家對感情的執着,抑或坎坷的境遇擠壓出他們深藏的鄕情,不管流落何處,他們的成就終究屬於臺灣。
最後我寫到王白淵,執筆之前還猶豫過是否應該寫他,在臺北的王夫人雲娥女士也說:「過去的人就讓他過去,何必再提呢!」但我還是提了,而且寫出了四萬字以上的長文來。
本書介紹的八位藝術家裏,只有陳澄波和王白淵兩人在臺灣過世,雖然兩人都到過中國,却有幸得以身葬故土。但「有幸」用來仍然是諷剌,因他們是帶着一身的「罪」離開這個世界,這與其他人又有何異,終究還是埋在地層下長年不見天日!
從王白淵的一生看來,他該是八人裏頭政治色彩較濃、社會使命感較強的一位,可惜本性裏仍脫離不開藝術家的天眞與浪漫。他之所以有「罪」,莫非也是那浪漫的氣質帶來的!文章裏我把他這一生分割成五個階段:㈠師範生時期,㈡詩人時期,㈢囚牢時期,㈣評論家時期,㈤治史時期。每一個階段都呈現出生命節奏的抑昂變化,這當中唯有詩人時期和評論家時期的王白淵才在他生命中奏出高昂的曲調,可惜這兩階段加在一起竟然不超出五年時間,而僅僅這五年,已足夠構成埋進地層的罪名了。
人總歸是要死的,早死晚死相差也不出幾個十年,黃土水和劉錦堂死時才三、四十歲,而且是死在異域,這是他們被人遺忘的主要原因。可是若將之與其他人的命運相比較,又發覺早逝者也未必是不幸,別人雖享有天年,却要受盡政治的折磨,在日本坐的是日本人的牢,在大陸坐的是共產黨的牢;在臺灣坐的是國民黨的牢,甚至還有人死在當政者槍下。藝術家稚氣滿滿、天眞浪漫,愛鄕愛民的熱情想壓也壓不住,但所愛若不是當政者之所愛,縱使不管政治,政治還是要管你。不論在太平或在亂世,不論他當的是臺灣的中國藝術家或是中國的臺灣藝術家,竟然沒有人能逃過政治這一關。政治何其霸道!更何況臺灣人還有與生俱來的原罪。
我背負着與他們同等的罪,提筆寫下這本書,而今付梓在卽,眞可謂百感交織。未知到底是我找到了他們,還是因他們而找到了我自己!
前天出版社打來電話,問我總共寫出多少人,我說總共有八人。又問,可否再增加兩人,使剛好湊成十人。我說八個豈不太多,你還希望有多少!對方終無語掛下電話。若不是與他們身負同罪如我者,安知多增一人,內心亦須多增一分沉痛!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紐約
作者 謝里法
謝里法,台北市人,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一九六四年赴法國,在巴黎美專學習雕刻四年,一九六八年離開法國抵達美國紐約,放棄雕刻,轉而研究美術理論與美術史,尤其研究台灣美術史最具功力,並挖掘出八位日據時代享有盛名卻被歲月淹沒至今不為人知的藝術家,範圍不僅限美術,還涉及文學、音樂等。謝氏對台灣美術史貢獻卓著,是活耀於海外文化界的著名藝術評論家。著有「台灣出土人物誌」、「重塑台灣的心靈」。
Posted in 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