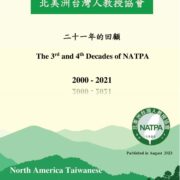此心安處是吾鄉
楊遠薰

喬治城街道風光,楊遠薰攝影
從盛夏至仲秋,接連獲悉幾位友人凋零,心有不捨,更有傷感。
縱使心知悲歡離合是人生必走的旅程,但回想起過往的相處與最後探訪時故友無奈的眼神,就心有戚戚。這種心緒在入秋的季節、雨濛的時分尤其時起時落,如薄霧,牽牽絆絆。
幸好上帝很仁慈,不管發生甚麼事,太陽總繼續東升。在一個霪雨過後的午后,看到太陽穿越陰霾的天空,散放出燦爛的光芒,我頓時覺得該是抖落惆悵、到外頭追尋陽光的時候了。
我與阿加於是走訪我素來喜愛的喬治城 (Georgetown)。
喬治城瀕臨波多馬克(Potomac)河,成立於1751年,比美國首都華府(Washington, D.C.)的建城還早半世紀,迄今已有270年歷史,但仍充滿魅力與活力。
華府於1801年建都後,喬治城成為其一部分,與岩溪 (Rock Creek) 對岸的地方共同形成華府富饒的西北區。不少富裕人家於美國鍍金時期 (Gilded Age) 在此區興建維多利亞式的城堡房子,如今有的仍保留,有的則改建成現代的大廈。
我們沿著 31街南行,走往熱鬧的華盛頓港口(Washington Harbor)。由於萬聖節 (Halloween)將至,許多房子的門前都有 一些別出心裁的裝飾。Q街的街角有棟古色古香的城堡屋,屋主在其二樓的陽台放置一隻巨大無比的長腳蜘蛛,在一樓的門窗前架起一面十分誇張的黑色蜘蛛網,顯然故意營造魑魅魍魎的氣氛。

喬治城風光,楊遠薰攝影
城堡屋的隔壁是一棟新式的大樓,但見每個窗戶底下都吊著各式各樣的鬼,讓人看了,不禁莞爾一笑。

喬治城的萬聖節景象,楊遠薰攝影
越接近市中心,房子越密集。許多人家的門前都擺置一顆顆的橘黃南瓜或刻有人臉的南瓜燈籠。
刻南瓜燈籠需要一點手藝與慧心。猶記初次到美國朋友家刻南瓜,我刻得很專注,也總算中規中矩地刻出個眼、嘴、鼻來,然後去瞧瞧別人的作品,發現怎麼有人把眼睛刻成斜的,把嘴巴刻成歪的?還有人把牙齒一顆顆刻得大小不一?不禁心想:為什麼自己就缺乏那麼一點創意與幽默?大概自小在刻版的升學教育下長大的緣故?

喬治城的萬聖節景象,楊遠薰攝影
走過繁忙的M Street,看到街道兩旁商店林立,不禁憶起淡水的老街。其實,華盛頓港就是從前的喬治城碼頭,座落波多馬克河口的喬治城猶如座落淡水河的淡水鎮,其瀕臨碼頭的街道自古即是店家與餐飲業密集的地方,路上行人熙來攘往。

喬治城的M Street,楊遠薰攝影
我們繼續走向水岸,瞧見河濱步道旁再度掛起了一團團的紫紅大花藍,不禁感到一陣喜悅。過去一年來,因為新冠肺炎肆虐,餐館禁止內用,港口一度冷清。如今疫情舒緩,人潮回流,但見每家餐廳高棚滿坐,步道上遊人如織,好似又回到往昔太平盛世的年代。

華盛頓港口風光,楊遠薰攝影
華盛頓港的噴泉廣場有著各式各樣的萬聖節擺設,包括澄黃的南瓜、褐黃的草堆、色彩鮮麗的秋菊、各種逗趣的假人、搞笑的鬼怪、以及故意佈置得陰森恐怖的鬼屋…等等。
有家餐廳的門口更豎立一尊身材高大、手披白色餐巾的鬼面侍者,笑臉迎接客人,成了招攬生意的最佳招牌。

華盛頓港口的萬聖節裝飾,楊遠薰攝影
萬聖節在美國是孩童的節日。每年十月的最後一天,孩子們打扮成各種鬼怪或動物,在入暮後沿街挨家挨戶地討糖果。從前孩子們在家時,每年十月一到,作母親的我就得幫他們張羅衣物;萬聖節那天,更得提早一小時下班,火速得衝回家,帶他們去Trick-or-treat…。
那些年實在很忙,既要戰戰兢兢地工作,也要當家庭主婦和媽媽,日子過得像旋轉的走馬燈。然後時光在忙碌中飛快過去,不知不覺,孩子們長大離家,也陸續擁有他們的事業與家庭,生活忙碌得一如從前的我們。偶而全家聚在一起吃個飯、聊聊天,就算享受天倫之樂。如今想來,這大概就是新版的「蕃薯不怕落土爛,只求枝葉代代傳」吧?

華盛頓港口風光,楊遠薰攝影
河畔有長椅,我們坐下來小憩,靜靜凝視著眼前的景致。波多馬克河河面寬廣,河水悠悠;名噪一時的水門(Watergate)大樓和美麗的甘迺迪藝術表演中心近在眼前。斜暉脈脈,我的思緒又不由自主得飄回這些日子來縈繞在心的一些事。
十月的第一個週日,我與阿加前往探望身體違和的林一輝醫師。我望著躺在病床上的他,問:「你怎麼了?」
「器官都壞了。」他回答。說這話時,他定定地望著我,誠摯認真的眼神一如往昔。
「甚麼地方不好?」阿加接著問。
「心、肺、腎和肝都不好。」他字字清楚地說,語氣中帶著無奈。瞬時,我感到一股哀愁。
我們不久告辭。林太太姿良一直送我們到車道,然後說:「一輝已在 Hospice (安寧) 中。」頓時,我們楞住,半响說不出一句話。
五天後,林醫師安詳辭世。
回憶過往,四十多年前,我們在俄亥俄州北部的一個白人小鎮相識。當時猶是美國新鮮人的我因病入院,與我素昧平生、長我十歲的林醫師和太太姿良照顧我,僅因我們同樣來自台灣。
後來,我們成為朋友,數度應邀到他們家作客。他們並且帶我們去參加克利夫蘭台灣同鄉會,引導我們認識更多的台灣鄉親。
一年後,阿加要到愛荷華州立大學就職,我們向他們辭行。原以為這短暫的相聚僅是一場萍聚,豈料三十三年後,我們在華府重逢,並且共同以華府地區為退休地。那種重聚的喜悅,真是不可言喻。
爾後的退休生活如金黃的秋天,美好但短暫。當北風吹起,黃葉便紛紛凋落。十月中旬,林一輝醫師獨自前往另一個世界。

好客的林一輝醫師伉儷(左四與三)經常邀請朋友到他家小聚。照片攝於2019年
一星期後,我們到林醫師憩息的地方,向他做最後的告別 (Viewing) 。因受疫情影響,那僅是個小型的聚會。幾對朋友陪著長眠的林醫師,娓娓敘談往日相處的情景。然後,大家一起去用餐。席間,有人問:「我們這一代台美人,死後骨灰該放何處?」
這是個敏感且見仁見智的議題,因此引起一些討論。提這問題的朋友說,他希望自己的骨灰能被送回台灣,安葬在祖塋,畢竟葉落總要歸根。但另一位朋友隨即應道,他要葬在美國,因為子孫都在這裡,這裡就是我們的新天新地。
我當時沒作聲,因為不曾想過這議題。但此時坐在波多馬克河的河畔,那問題竟不自而然地湧上。然後,我似乎聽到內心的一個聲音:「此心安處是吾鄉。」
沒錯,千年前,蘇軾被流放至嶺南猶處之泰然的朋友所感動,因此作詞道:「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 此心安處是吾鄉。」
那麼,我們這些在美國生活大半輩子的台美人豈不當如是?
據聖經的記載,亞伯拉罕接受神的指示,毅然離開在米索布達米亞的家鄉,迢迢跋涉至上帝應允的迦南地,在那裏建立了子孫繁多的以色列王國。這個故事豈不就是「此心安處是吾鄉」的寫照?
吾友林一輝醫師是第一屆台北醫學院的畢業生,在美國需要醫生的七十年代,到紐約接受訓練,然後在俄愛俄州任小兒科醫師長達四十年,退休後與太太搬到華府,含飴弄孫。他們一共有三個孩子、七個孫子,堪稱是第一代台灣移民在美國開枝散葉的典範。
我們認識林醫師時,尚無孩子,其時的美國於我是「他鄉」,在病中得到同鄉的照顧,真有「他鄉遇故知」的溫暖。三十三年後,我們在華府重逢,彼此興奮地分享兒孫的照片,這時的美國對我們來說,已是「吾鄉」。其實,生活就是家庭、工作、朋友、鄉情與在地人文、景觀…等的混合,層層疊疊,交織在一起,久了之後,竟也習慣了這種東、西文物混雜的多元與繽紛。
若念及此,那麼死後的骨灰該放何處或如何安葬,於我好像不那麼重要。我毋寧在有生之年,認同這個心安之處,歡喜地與身邊的人共過有意義的生活。
也因此,在這金黃的秋天,我懷念故友,但也願以陽光之心,珍惜現在所擁有的,和孩子們共同迎接即將到來的感恩節。願主賜福,讓我們繼續向前。(End)
Source From: http://blog.udn.com/Carole777/170566195
Posted on 11/30/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