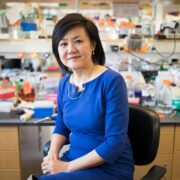離鄉
作者:吳木盛
老人與少女斷斷續續地在談,大概已談了數小時,話是那麼多,好像有談不完的話料,他們的話語擾亂著四週的寧靜,偶爾也打斷我的思路。汽車仍是不停地向前奔馳,冷氣機吹來的冷氣使身體感到一點舒適,但還是幫不了惡劣的精神。
又想起了懷妊的妻子及不滿一歲的孩子,這個時候,他們在睡吧?也許妻子正輾轉不能成眠?孩子哭著要爸爸?把一個沉重的擔子交給了妻子,不但沒留給生活費,還留給了一筆婚債。她是一個堅強的女子,不但勇敢而毫無怨言地承負起了重擔,還一直鼓勵我,眞想知道此刻她內心裏想的是甚麼?我眞對不起她。
汽車在無人煙的地方急馳著,車外是一片沙漠,除了遠處的一座沙山靜靜地坐在那兒及偶爾可以看到的仙人掌以外,這一部灰狗車是絕對的孤獨。一切是那樣陌生,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在地獄。由鏡子看到戴太陽眼鏡而全心在駕駛的司機。
孩子、妻子、父母、親戚、朋友,離開時的依依,故鄕——那養育我的地方……一而再地出現在腦際,只離開了二天,鄕愁已有萬斤之重,心身疲憊,臉部濕濕地,啊!我哭了,爲此我有一點震驚。朦朧中又想起了已決定數次不再想的債務,眞是滿身的債,身著的西裝、口袋裏的現金、保證金、機票、車票都是債,加上結婚時借的債,債債債……。每次想起總覺不安又焦急。
很靜,老人與少女不再談了,大概是睡著了。
車停了,跑上來個警察,走到我面前時,停下來了,看到警察我有一些緊張,但他的客氣緩和了我被攪亂了的情緖,他很有禮貌地向我說了一些話,沒聽懂,但毫不猶豫地,我拿出了護照,他翻了一會後,點頭說聲多謝就走了。假如早知道會走上留學這一條路,早該把英語的基礎打好的,我反覆地吿訴自己。
一年前才興起出國的念頭,那是把自己的前途宣判死刑以後的事。在此以前,一直相信自己是沒有資格亦不該出國的,除了無能籌足出國費用及得交給妻子難於肩負的包袱以外,也得交給年老而多病的父母親生活的重擔,四個弟弟正在長大也正在受敎育。然而離開了大學五年以後,我發現除了出國以外並沒有其他的選擇,五年的時間使我看淸了像我這種無背景、不善鑽營、不願入黨的,前途只有死路一條,尤其是最後一年,過得很痛苦,那一些發霉而無色無彩的日子在生命上覆上了一層陰影。我想到留學,唸一些書回來敎書,將一生埋於尋求知識及敎育,可能是我該走的路。
「在那無親無戚的所在,即使是做皇帝也無意思。」岳母在機場的話別又浮上了腦際,雖然機場的噪音那麼大,但她說的每一字却深深並牢牢地釘在我心靈的深處。「不必擔心,三年後就會回來了。」我是如此肯定地回答了她,她的眼睛早已浮現了幾個斗大的眼淚。
我是該將岳父送的禮金收起來交給父母的,我又吿訴自己一次,有了那一筆錢,他們就可以到台北送我。他們眞可憐,竟窮得連往機場送愛子離開的旅費都無法籌足。知道岳父的事業經營得不順利,無論如何我是提不起勇氣接受他的厚意的。
老人又開始講話了,大概是中午了,陽光不直射進來了,不知從何處傳來了音樂聲,是「Skiyaki」,在一切都陌生的怕人的環境下,那熟悉的調子竟是那樣親切。我張開了眼睛,沙漠已不知去向,浮現在眼前的是整齊的街面。好像很熱,人們著短衣,大概已接近墨西哥邊境,很多墨西哥人,建築很西班牙式。眼皮是太疲倦了,只張開了 一會又合起來,好奇心被疲勞所征服。大概已將近廿多小時沒吃、沒喝也沒睡了,自落山磯一上車就醒到現在,旣餓又渴,右鬢部有一點痛,腦筋還算淸楚。頭有一點熱,是與座椅磨擦所引起的,在落山磯時應該借個枕頭的。
六年沒唸書了,學校已開課二個多禮拜,英語又是那麼差,不知跟得上否?愈想愈沒信心,英語差大概不會構成太多的困難,在大學時沒有幾門課是在敎室學的,不管是因爲語言不懂或敎授的不學無術而引起的,沒聽懂敎授的課的效果都是一樣。一想到大學的敎授,很自然地嘴角微動了一下,啊!我又在駡人,我在駡那誤人子弟及謀殺英才的一群。
車子慢下來了,大概要進站了,這一次一定要下來吃一點東西和喝水,即使吃不到東西,水是一定要喝的,也一定要上廁所。
整理一下外表,稍微不穩地下了車,走入車站賣點心及午餐的地方。觀望了一下,終於看到有人在炒蛋。心想:二個炒蛋、一杯牛乳加一個蘋果雖不很飽,但已夠充飢,袋裏還有六十多元的現金,只要沒有意外,到學校是不會有問題的。於是跑到蛋攤前排隊。中午,人很多,但爲沒有吵雜而感到意外,隊伍相當長,但有條不紊,沒有人揷隊。到番時,我要了兩個蛋,她問要Scrambled, Sunny side up, Turn over?聽不懂,被問得發窘,在那麼多人的面前左不是右也不是,終於沒有買就退隊了。看到一位黑女孩在飮水器(Fountain)用水,我走了過去,口甚渴,不眠使咽喉更乾,是平生第一次用飮水器,以爲是光電自動器,所以彎了腰就想喝水,但水並未自動跑出來,在做第二次的嘗試時,由眼角看到那一部由落山磯坐過來的灰狗車揚麈而去,這一驚非同小可,口再也不渴,肚子也不餓了。行李、書、保證金等都隨車而去,剩下的只有袋裏的現金、車票及護照。看看車站的掛鐘及時間表,確確實實離開車的時間還有幾近半小時,然而車却走了。緊張、驚訝又焦急。我開始到處找同車的旅客,老人及少女早已不知去向,一位黑女人好像是同車客,但沒有把握,還有一位年輕人好像也是,但也難肯定,怎麼辦?
「行李有學校名,亦有台灣的地址,無論如何是丟不掉的,坐下班車子到學校時,行李可能已在學校等著。」我如此地安慰著自己。但不久念頭又轉過來了,假如丟掉了怎麼辦?台灣旣回不了,美國也待不下去。
假如有錢坐飛機由落山磯直飛棉花城就不會有這種麻煩了,也早已上課了……,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那一部車子却在遠處出現了,它跑回來了,大概去灌汽油吧?興奮、歡喜、雀躍,但却仍是憂喜參半,不知是不是同一部車子?一直到看淸楚掛在車上的目的地——棉花城時,才放下了心。然而當車子停下來時,我發現換了司機,而且車子好像也不是由落山磯開來的那一部,假如換了車,那我的行李呢?我開始懷疑所有的一切,一切變得那麼不可靠。
車子慢慢地在動,又要出發了,還要廿七小時才到棉花市,我的行李呢?又多一項擾人心事。父母、妻兒、親戚、朋友、學校、債務、行李……又不停而反覆地惱人。
——原載《台灣文藝》一九八六、八、十五
摘自 第四樂章 199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