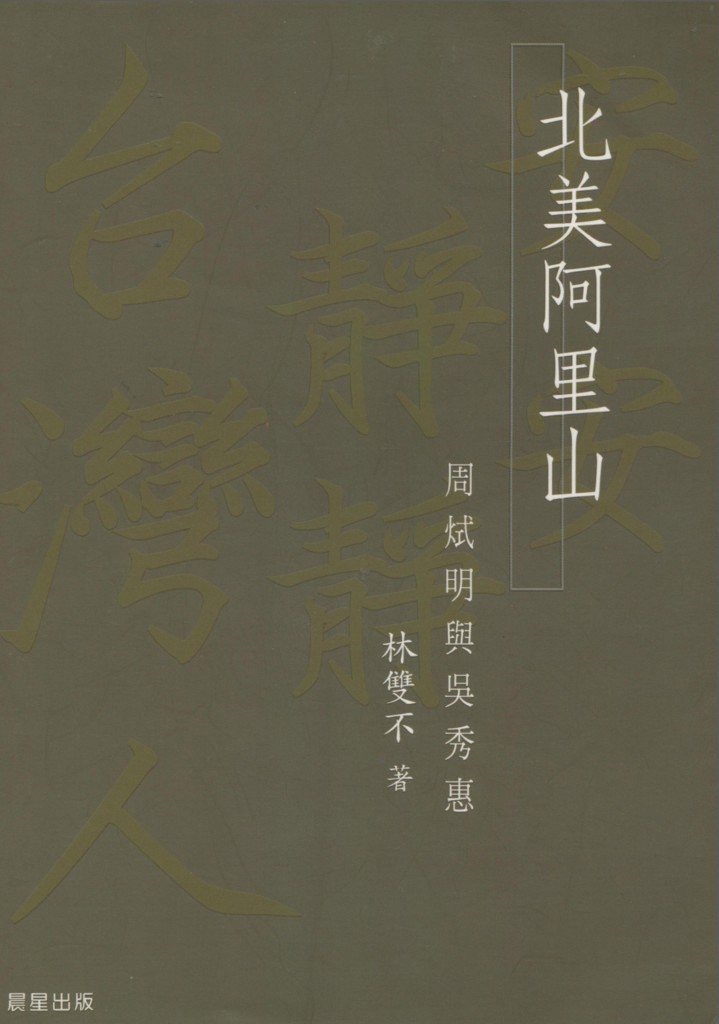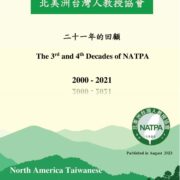北美阿里山-周烒明與吳秀惠
作者 : 林雙不
周烒明與吳秀惠
一九四九年五月初,朵朵白雲在群山綠樹之間 舒緩伸展的一個晴天午後,周烒明、吳秀惠在阿里山初遇…。
一九九四年夏天,一個陽光亮麗的晴朗午後,周烒明坐在美國波特蘭的二樓居所窗前畫畫,燦爛的視野遠處,朵朵白雲在群山綠樹之間舒緩伸展
周烒明出聲驚呼叫來吳秀惠,指著窗外:這是四十年前他倆相遇的風景。
於是,他們把這座山稱作「阿里山」。
台湾人生活圈的許多同鄉都知道美國有一座阿里山,在波特蘭,在奥立岡,在北美洲,在周烒明和吳秀惠的內心深處•
自序
終身反對的文字工作者的反對小說
在台灣極度封閉黑暗的年代裡•在海外有一群不求名利的人冒著身家性命的危險
企圖為故鄉的前途點燈,隨後慘遭黑名單阻隔,淚眼望斷鄉關,飽受親情與人性的悲慘折磨!
林雙不以文學創作筆法,將這一群默默奉獻於海外台麫獨立運動的小人物故事,寫成了「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小說,透過這些安安靜靜台湾人的一生故事,呈現海外台湾獨立運動的種種。
不管在哪裡,對鄉土台灣真摯的愛永遠不變,台灣永遠是他們的唯一。
1
終於決定出版《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小說,我最明顯的感覺
竟然是艱苦。
記得靑澀年少的十九歲,第一次決定出書,而且一口氣同時出版三本時,感覺是無比興奮,好像整個人都要飛起來了一般。三十一年之後,回想奮時的感覺,依然那麼強烈鮮活。爾後陸陸續續有書出版,感覺大抵還是愉快的;就算後來出多了,有點麻痺了,至少還能維持平靜,不喜不懼;實在想像不到,年近五十的此時此刻,決定要讓《安安靜靜台灣人》和台灣人見面、向台灣人請敎時,感覺居然如此天差地遠!
旣然出版這套書的感覺是這麼不愉快,爲什麼不要乾脆不出?假如心境修爲能夠這麼乾脆,哪裡還會滋生艱苦?矛盾的心情眞是說來話長,如果您已決定讀完這本書,甚至這套六本書,就請您容許我佔用一點您的時間吧,謝謝您。
2
動念寫作《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是九五年夏天的事。那年七月,我應邀參加一年一度的台灣同鄕會美東夏令會,做一場演講。八六年以後,我已經多次參與類似的海外台灣同鄕聚會,認識了不少鄕親序大,感覺相當親切。特別親切的是,九五年聚會的場地在美麗的康乃爾大學校園,以前我也曾經來過。
聚會的一天夜晚,我參加台獨聯盟資深盟員在一楝大樓地下室舉行的一場回顧座談。數十位各行各業極有成就的年逾半百盟員散坐在地下室的角落裡,輪流回想述說聯盟三十多年來的點點滴滴,就算是最艱困最痛苦的往事,經過歲月的洗滌,似乎也都顯現奇異的欣慰、快樂與溫暖的光芒。我靜靜坐著,靜靜聽著,靜靜感動著。就是這群人,在台灣極度封閉黑暗的年代裡,冒著身家性命的危險,企圖爲故鄕的前途點燈;也就是這群人,隨後慘遭黑名單阻隔,淚眼望斷鄕關,飽受親情與人性的悲慘折磨;當然也是由於這群人,長久無悔的堅持和打拚,讓台灣島的前途,逐漸露出獨立的曙光。然而這群向來不求名利的銀髮族,卻也逐漸即將消失沒入台灣歷史的塵埃當中。這是不公平的歷史必然;自來總是搶奪到現實權勢的人,同時搶奪到歷史的撰述與詮釋的權力。當然,這群人應該是不在乎的,可是我在乎,我爲他們在乎;做爲一個終身反對的文字工作者,保留平民的生活記錄,責無旁貸,我怎麼能夠任令他們消失,反而縱容那些打著台灣運動招牌、追求個人名利的投機份子,踩過默默奉獻的同志的靑春與熱血,篡取歷史的光環?
歷史的考量之外,還有現實的必要。九〇年代以後,由於台灣島內部份高舉台灣獨立運動旗幟的政治人物或政治動、植物,基於我們無法知悉的種種動機,對於運動的堅持或實踐,漸漸打折,甚至偏差。平常私底下滿口獨立建國,一旦碰到選舉,就不講了,說是會嚇走選民;萬一當選,當然就更絕口不提,還胡言亂語,宣稱台灣獨立只能做不能說;原本似乎是生死追求的理想,忽然變成騙取選票、爭奪利益的口號。這種赤裸裸的敗德行徑,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失去台灣人民對獨立運動的認同與支持。許多原本熱心奉獻的參與者,開始懷疑部份運動同志的純度,甚至對於整個獨立建國運動的前景,失望洩氣,誤會所有獨立運動工作者都差不多,都有個人的名利私心,都不是口頭上眞正的無私無我。這麼嚴重的誤解,當然需要導正;假如能夠提供他們一些正面人物的故事,應該會發揮一點作用吧?歷史的思考以外,這無疑是現實運動的必要。
座談會的主持人最後要我講話,說因爲我是唯一一個靜靜聽到天快亮的非盟員。我簡單講出自己的感動,同時請敎他們,願不願意讓我把他們的故事寫下來,歷史層面,做爲海外台灣人獨立建國運動史的一部份,現實層面,也做爲台灣島內繼續推展台灣獨立運動的精神助力?他們同意了,還慷慨的同意我的請求,委託與我相熟交好的聯盟中央委員莊秋雄先生和我商量細節。
我很快與莊秋雄達成共識。故事的寫作以個人做主角,以運動做背景;透過幾個人物的一生,盡量鋪陳整個運動的面貌。人物的選擇標準是,長久投身海外獨立建國運動、出錢出力沒有出名、沒有參與過台灣選舉、沒有利用運動求取一己名利的;也就是默默獻身、打拚做事不說大話、不計個人安危毀譽的;我把這種人定義爲「安安靜靜台灣人」。我和莊秋雄的共識就是要透過這種安安靜靜台灣人的故事,呈現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的種種。不過我淸楚知道,受限於主觀的學翻客勸糖’雛纏這件事不可能韻歷史記錄,只能是歷史的一部份;再說我的興趣在文學,在描寫人,人的意志、人的精神等等’所以我傾向於運用文學的筆法來表現。我要寫的,是小說,不是傳記;我沒有企圖記錄歷史的一五一十,然而也沒有興趣寫作完全虛構的小說,我想寫的,是根據事實自然發展的小說,所有的人物,包括主角或相關角色,我一律會使用名;地名也一律不做更動。我希望完成以後的作品當中,有歷史也有文學;甚至在完整表現人物意志和精神的考量底下,必要時,我寧可偏重文學,而議歷史暫時委屈、稍微消隱。
我和莊秋雄開始尋找適當的人物,希望進行訪談,蒐集資料。這些可敬的人物有4些是我多年來接觸過,有一定的瞭解,深深敬佩的;有些是我沒有機會認識,不過莊秋雄知道甚深,極爲肯定的;當然也有幾個,就是夏令會時在康為爾親身參加座談的前輩。我們把名單列出來,由莊秋雄聯絡。說明我們的想法與預備的做法,希望得到對方的協助。有的人很謙虛,說不値得寫;有的人有顧慮,說不方便寫;有的人沒興趣,直接拒絕。一番折騰以後,初步確定了八個名單,包括一個已經不幸亡故的。莊秋雄說,應當寫的人還很多,慢慢再聯絡,就先做這八個;不在人世的,聯絡她的兄弟。
九五年十月,開始訪談。美國很大,八個人散居各地;冬天的風雪我很不習慣,長久的抛妻別子孤單旅途我也很不習慣。我飛來飛去,住在他們的家裡打擾,抓緊他們下班之後的分分秒秒,追根究柢,壓榨他們臨老的記憶力;當然包括他們的配偶、家人或知交,而且,延續到九七年的秋天’長達兩年,一次又一次;必定是他們的熱誠一再溫暖我孤寂的心吧,不然我怎麼有可能堅持?必定是他們對於故土台灣超乎常人的關懷與摯愛吧,不然怎麼有可能忍受我再三的騷擾?爲了答謝他們的好意,也爲了對歷史和現實負責,我在進行訪談之前都先跟他們說淸楚,如果他們有什麼顧慮,不希望或不方便公開的情節,都請不要吿訴我,這樣比較不會影響我下筆之前的佈局;我知道,旣然寫的是歷史性的小說,除了主角之外,當然不可避免會牽涉到許多同時代的人物,特別是一起從事獨立運動的同志;人總是人,有感情之私,某些事情不想公開,可以理解。還是爲了對歷史和現實負責,我同時答應他們,如果天公保庇,眞的能夠把小說寫出來,一定會讓他們先看過初稿,獲得他們同意以後,再設法發表、出版。
九七年十一月初,我感覺可以寫了,就把自己關在員林自家三樓的書房,面對電腦,開始寫作。爲了絕對專心,爲了全力投入,整整半年時間’我沒有走出過家門一步,沒有接過任何一通電話,妻子女兒對外總是說,我又出國了。甚至有一次家父家母來員林小住一個禮拜,都不知道他們的兒子就在三樓閉關隱居;當然,一輩子不認識半個漢字的他們,是不會上三樓書房的。每天幾乎天一亮,我就開始打字’除非精疲力盡,很少休息。打著打著,覺得這些可敬的台灣人就在我的身邊呼吸講話,隨著他們的情緖起伏,我笑我哭我嘆息;打著打著,覺得這些可敬的台灣人周邊的相關人物也在我的書房裡漂浮,有的很可愛,有的很可惡,甚至不只是可惡,是卑鄙是無恥!只好一再提醒自己,暫時置身事外,盡可能還原眞相,讓歷史的歸於歷史,讓現實的歸於現實。如此繼續半年多,當我打完最後一個故事,重新走出家門時,台灣島的五月天,陽光已經非常亮麗燦爛了。
隱居半年,總共打寫將近一百萬字。很久很久了,追隨可敬的前輩,投身台灣獨立建國運動之後,沒有心情、沒有體方、沒有時間從事我這世人最喜歡、也認爲最有意義的小說寫作,已經很久很久了。能夠順利寫完《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對於矢志終身不參加任何政黨、不參與任何選舉的一個文字工作者而言,即使不去談論作品的種種,光是完成作品本身,都已經是我垂老生命的再生了。我的狂喜與激動,跟五月的陽光同樣亮麗燦爛。
總名《安安靜靜台灣人》的這一百萬字,我把它分爲六册。前五册都是長篇小說,分別描寫邱義昌先生(篇名《無厝的渡鳥》)、莊秋雄先生(篇名《深秋天涯異鄕人》)、楊宗昌先生(篇名《南屯樸麗澗》)、胡敏雄先生(篇名《胡厝察與茉里鄕》)和周拭明先生(篇名《北美阿里山》),第六册包括兩個中篇和一個短篇,分別描寫王博文先生、鄭啓賢先生和不幸已經身故的黃聰美女士(書名就用系列名稱《安安靜靜台灣人》)。完稿的刹那,心中想到莊秋雄當初說過的,應當寫的安安靜靜的台灣人還有很多,忍不住就開始幻想;幻想這套書出版以後,產生良性反應,更多人主動再跟我或莊秋雄聯絡,找到更多不棄嫌的,讓我有機會繼續訪談繼續寫。假如幻想果然成眞,我的垂老之年就有喜歡的、有意義的事情可做,不會完全浪費台灣人種米種菜餵養沒有路用的我了。這樣的期待或幻想,也讓我的感覺激動狂喜、亮麗燦爛。
完成初稿的一個多月以後,我非常興奮,搭機飛美。我迫不及待飛東飛西,把初稿的電腦磁片一片一片,分別送到當事人的手中。我多麼希望他們能夠分享我的激動與狂喜;特別是,我多麼希望他們瞭解,這件事是我們共同合作完成的,因爲相同的歷史理念和現實目標,辛辛苦苦,合作完成的。我多麼誠懇希望,他們和我一樣,期待這套書的完成、發表與出版,能夠爲日漸衰微的台灣獨立建國運動,注入一針強心劑。我一個一個興奮吿訴他們,只要他們看過初稿,沒有太大問題,同意發表,我返台之後立刻開始安排在報章雜誌上的發表事宜,然後在公元二千年十月全套出版。我跟他們講,之所以先要發表,一方面是爲了引起注意,另一方面是爲了賺點稿費;沒有發表,就沒有稿費。我說自從投入建國運動以後,作品幾乎全面遭到封殺,難得有機會發表,很少賺到稿費。直接出版不少書,只是擔心賠累出版者前衛出版社,當然也不敢要求版稅。以前還在敎書,有一份固定的薪水,沒有稿費沒有版稅我可以不在乎。九四年夏天辭掉工作,從此就毫無收入了,所以希望先發表,也是私心貪財的意思。至於爲什麼必須等到兩千年十月,也有兩個原因。一是將近一百萬字的作品,就算順利找到報章雜誌願意發表,連載完畢也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二是私心的,因爲屆時我這個無用的生命,正好滿五十。
想到年滿五十時,我可以出版一套六册向台灣歷史與現實交代的系列小說《安安靜靜台灣人》,在遙遠異鄕孤單的夢裡,我都會禁不住激動大笑。原來文學寫作就是我的最愛,我活著的意義與目的。我多麼希望在有生之年,親眼目睹台灣獨立建國成功以後,把政治事務放心交給有能力、有興趣的同胞去做,然後飄然歸隱,專心寫作。
八月返台,開始等待。回音普遍不好,有些是當事人記憶有誤、資料偏差,有些是當事人當時講了,爾後發現不方便,還有絕大一些是,當事人沒什麼,但是家屬有意見,而當事人不願意讓家屬不滿。怎麼辦?必須改。資料偏差的,修正;記憶有錯的,訂正,一般來講比較容易;可是訪談當時已經講了,我也已經當做小說素材醞釀處理了,忽然需要抽離,就好像做菜時已經加入調味品,做好之後才要抽掉,我的能力低微,就沒有辦法處理了。至於家屬的反應,當時就沒有考慮在內,人數又多,個個重點不同,要修改到人人滿意,我絕對只有高舉白旗。
怎麼辦呢?難道就不要發表出版了嗎?難道就不要動念之初所期待的理念與目標了嗎?歷史上留下記錄,現實上互相鼓舞,雙方面的渴望都要放棄了嗎?個人寫作生命的重斩萌芽,長時間的海外奔波,背離人性的書房閉關,都要白白忍受了嗎?努力修改,盡量讓大家滿意吧!一天又一天,同樣面對冰冷的電腦,面對幾乎不可能的任務,春天不再,夏天隱去,秋天匿跡,我的生命裡,只剩絕望冰冷的冬季。狂吾激動之後,絕望令我無法承受。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沒有期待,我所擁有的,只是憂鬱,只是愁苦,只是一大串無法想通的爲什麼。爲什麼當初我會動念做這件事?爲什麼莊秋雄要好心幫我聯絡?爲什麼這些可敬的台灣人不能爲了共同的理想與目標,斷然拒絕世俗人情的顧慮,以及家屬的阻撓?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
九九年中期,在經過長期的自我調適、困苦修改,仍然無法獲得當事人及其家屬的滿意以後,我被迫決定放棄。就當做不曾做過這件事吧,不要再想到什麼發表、什麼出版,反正已經慘敗的人生,多一次失敗算什麼?不能讓當事人不好做人,他們都是那麼無私犧牲的,那麼値得尊敬的,而且當初都是一而再、再而三接待過我,容許我多次追根究柢肆意干擾的;我敬重他們的大我奉獻,也珍惜這樣的小我私情,怎麼可以讓他們困擾?乾脆就放棄吧放棄吧!
3
兩千年年初,主角當中有人返回台灣,非常富有同情心地問起這個系列小說的情況,說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覺得就算出版了,他也不會很在意;至於家屬的不滿,他相信也不可能太過持久。他說反正只是記錄那些曾經發生過的事實而已,了不起爲了文學效果,有時縮水有時膨脹,應該都是能夠忍受的。再說雖然都是使用眞實姓名、地名,可是所謂的「眞實」,也只有對那些原本就知道的讀者有意義,數十年之後,眞不眞實怎麼再去區分、還剩多少意義?比如說「莊秋雄」三個字,這個年代認識他的,當然知道這是一個眞實人物的姓名,可是不認識的呢?或者三、五十年以後呢?「莊秋雄」這三個字也許已經和「卡拉馬助夫」或「劉阿漢」一樣,只是一個小說角色的名字而已,誰還去計較他的眞眞假假?重要的是,這一代海外台灣人爲了家園獨立建國所展現的意志與精神,不能被抹煞;尙未完成的台灣大業,更必須持續。他說意志與精神最重要,其他枝枝節節,不必太在乎。他說人在做天在看,日久見人心;只要秉持眞理勇往直前努力去做的事,不會永遠被誤會。他鼓勵沮喪的我,再想想看,適當的時機,就直接發表、出版吧。
三月中旬,台灣人民選出陳水扁做總統了;表面上,台灣人長久以來追尋的獨立建國目標,似乎跨前一大步了。不過,陳水扁迅速表白他的「台灣心、中國情」,接著一再宣示他不會宣佈台灣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廢除所謂的國統綱領,而且沾沾自喜,誇耀自己是「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以及毫無台灣立場的內閣人事佈局等等,顯然淸楚昭吿天下,台灣的獨立建國大業,還必須另有期待。陳水扁的表現我絲毫不意外,意外的是,台灣人民的抉擇,給了我發表、出版《安安靜靜台灣人》的適當時機。獨立建國運動必須繼續做,覺醒的少數台灣人需要默默奉獻、安安靜靜、無私無我的典範。時間不多,等不及先行發表,等不及貪財賺稿費,就直接出版了吧。眞巧,完稿之初預計出版的曰子,也正是同一個時候。
大我的必要,讓我決定出版。小我的私情,讓我愧對部份可敬的當事人。大我小我的衝突矛盾,造成我心情特殊的艱苦。
做爲終身反對的文字工作者,還是以大我爲重吧。一己的艱苦和伴隨出版以後可能面臨的責任,我個人願意承擔,當然,我迫切期待海外島內衆多安安靜靜的台灣人站在我這邊,深深鞠躬,非常感謝。
(2000年6月6日寫於員林)
作者 林雙不
 本名黃燕德,一九九五年改名黃林雙不。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八曰出生於雲林沿海的東勢厝。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畢業,曾任職遠景出版社、員林高中教師。
本名黃燕德,一九九五年改名黃林雙不。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八曰出生於雲林沿海的東勢厝。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畢業,曾任職遠景出版社、員林高中教師。
小學五年級開始投稿,中學時代開始以「碧竹」為筆名,發表詩、散文、小說。八〇年代更改筆名為「林雙不」,作品風格丕變,一改以往感性生活的抒情筆觸•而專注於關懷社會以及文學評論工作。九〇年代前後,積極參與政治、社會運動,發表街頭演說。一九九四年辭去教職,並開始寫作以「安安靜靜J為題的創作。一九九七年十一月閉關寫作「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小說。曾獲文復會金筆獎、中阈寫作協會文藝獎章、聯合報小說獎、吳濁流文學獎、賴和文學獎等。
作品有小說集《決戰星期五》、《大佛無戀》、《大學女生莊南安》、《小喇叭手》,散文集《事事關心》、《安安靜靜很大聲》、《安安靜靜想到他》,新詩集《台灣新樂府》,演講時論《大聲講出愛台灣》、《林雙不短打》等六十幾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