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金山灣區台灣之音主持人
黃介山先生訪談紀錄
何義麟
2020年3月
臺灣風物第70卷第1期抽印本
149-172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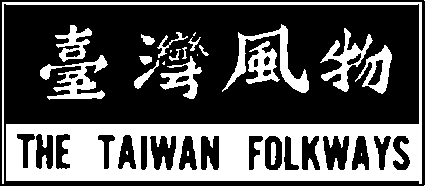
目 錄
卷頭語/詹素娟…………………………………………………………. 6
珍貴史料
一份百家姓文件、兩張古文書──解開西拉雅族
Akatuang 家族史的謎/Alak Akatuang 段洪坤………………. 9
論 著
大量觀察──日治時期臺灣的統計調查與人口管理
/林佩欣……………………………………………………………… 15
日治時期臺灣人印刷業的發展──以臺北市為中心
/許芳庭…………………………………………………………….. 53
4 臺灣風物 70 卷 1 期
許子秋任省衛生處長時期的霍亂防治(1962-1970)
/陳世局…………………………………………………………….. 95
口述歷史
舊金山灣區台灣之音主持人黃介山先生訪談紀錄
/何義麟…………………………………………………………… 149
通 訊
活動報導/陳鳳華………………………………………………….. 173
出版消息/杜曉梅………………………………………………….. 181
臺灣風物 69 卷總目錄………………………….. 197
舊金山灣區台灣之音主持人
黃介山先生訪談紀錄
何義麟
訪問/記錄:何義麟
時 間:2016年12月27日 下午13:30~15:00
2017年6月30日 上午10:00~下午13:20
2017年9月07日 上午10:00~下午16:00
2019年8月22日 下午13:30~下午16:40
地 點:美國帕洛奧圖(Palo Atlo)黃介山自宅
受訪者簡介
黃介山先生(1935- )是舊金山灣區臺灣人社團之主要幹部,在臺灣協志會、臺灣同鄉聯合會等團體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同時也積極參與臺語教會之事務。由他主持的「灣區台灣之音」,推進臺美人聲援臺灣民主化運動,貢獻卓著。因此,口述訪談紀錄之內容,首先將介紹黃介山先生的生平事蹟與灣區臺灣人的社團活動,而後進一步討論高雄事件之後,灣區如何建立起台之音,並請本人說明這個電話錄音傳播站的運作詳情。
1970年代,臺灣黨外運動逐漸興起,並與海外臺灣人社團建立聯繫網絡,舊金山灣區的臺灣人社團當然也不例外。l977年間,紐約的臺灣鄉親採用電話錄音的方式,名為「台灣之音」,宛如電臺一般播報臺灣島內的最新消息,最初目的是聯絡鄉親情誼。然而,隨著臺灣的國際處境日益艱難,島內外聯繫更加緊密,台灣之音很快就成了臺美人聽取島內消息的重要管道。1979年美國與臺灣政府斷交前後,海外臺灣同鄉憂心臺灣前途,各地同鄉會開始「轉播」紐約台灣之音的電話播音,以節省打長途電話收聽的費用。舊金山灣區也不例外,同樣設立這種電話錄音的轉播站,甚至進一步創立自己編輯採訪的「灣區台灣之音」。
從1979年4月1日起到1982年12月底為止,黃介山擔任「灣區台灣之音」的負責人,從撰稿到播音等全部一手包辦,而且完整保存當時的廣播稿。其播音起訖時間,正好涵蓋發生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等,島內政局出現變局的時期。電話錄音的內容,見證了海外臺灣人對島內情勢變化的認知,以及社團與個人所採取的行動。2016年底,筆者透過石清正先生之介紹,得以前去拜訪黃介山先生並進行訪談,同時取得其親手寫下的台灣之音播音紀錄手稿。希望這份訪談紀錄,能夠讓大家更清楚認識舊金山灣區臺灣人的社團,以及灣區台灣之音的播音活動。了解這段時期的變化,也可見證臺灣民主化歷程的轉折。
一、樹林的童年生活與求學經歷
我是1935年(昭和10)在臺北州海山郡鶯歌庄的樹林出世,黃家是樹林的大家族,我祖父黃煙春是地方的名人,在當地最有名的人是黃純青,他算是煙春的叔父。但是,到我父親這一代,我們這一房就沒落了。我爸爸黃元,1930年(昭和5)臺北第二師範學校畢業[1] 之後,開始擔任公學校老師。1934年跟我媽媽結婚,然後連續生了三個小孩。我媽媽不幸在1939年就去世了,我是家中的長子,媽媽去世那年才4歲,隔年我爸爸也過世了。因此,我們家三個小孩,包括我、妹妹妙芬、弟弟介洋三個小孩,都交給阿公、阿嬤來照顧。很不幸地,父親過世後兩年,就是1942年時,我阿公也過世了。所以,實際上我們都是由阿嬤扶養長大。阿公過世後,遺產處理得不好,結果很多財產被侵吞了。還好,我們幾個小孩子都還能繼續上學。日本時代我讀到國民學校四年級,日本就戰敗投降了。但後來,我還持續地進修日文,因此日文程度還算不錯。由於有這項語言能力,對我後來求學與工作很有幫助。
1947年那一年,我從小學畢業,然後升上建國初級中學,1950年轉入我姑丈執教鞭的泰北高中部就讀,1953年畢業。高中畢業後,因為沒考上大學,所以就到臺大農化系擔任雇員,當時雇員雖然只是約聘人員,但薪水待遇非常好。1957年時,我考上法商學院(中興大學)的行政系,並順利在1961年畢業。大學畢業後就去服兵役,擔任預備軍官一年。隔年1962年,我通過教育部的留學考試,同時也拿到入學許可。但是,不知道是甚麼原因,到美國大使館辦手續,都無法拿到赴美的簽證。因此,我就先到雄獅鉛筆公司的外務部上班,負責結匯的業務,當時我的英文程度還算可以,工作也勝任愉快。
因為留美簽證沒辦法順利取得,無法立即出國,所以就決定在1962年先結婚。我太太郭秋薰是南部人,她來到樹林長老教會附設的山地女青年保母班當教學主任,兼教鋼琴。因為這樣,我們才有機會在教會認識。這個保母班是孫理蓮牧師娘[2] 開設的,為山地培養不少人才,對原住民社會貢獻很大。我家原本不是基督教徒,家族裡面只有姑媽是信徒。聽說姑媽在小時候感染了傷寒,受到馬偕的醫治之後,才成為信徒。
我會成為基督徒跟姑媽受洗沒有關聯,我是因為樹林教會就在家的對面,年輕時候就常去教會。而後,又跟著美籍姑娘上Bible study的課程,原本只是想要藉由讀聖經來學英文,但經過一段時日後,很自然地我就受洗變成基督教徒了。後來,我的婚禮就在樹林長老教會舉行,在我出國留學前,我跟我太太已經有兩個小孩,女兒是1962年底出生,老二是男孩,1964年出生。

圖1 黃介山、郭秋薰夫婦結婚家族合影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
出國前,我很積極參加教會的活動,結婚後先擔任樹林教會的執事,也帶領過教會的團契,直到1965年出國為止。雖然我出生在樹林的大家族,但是後來我們這一房變得很單薄,我弟弟也定居美國,只有妹妹結婚後,還住在樹林的老家。妹妹是跟一位外省來臺的軍人結婚,婚後兩人就在樹林鎮博愛街的老家經營雜貨店兼租書店,店名為「蘭亭書屋」。解除黑名單的限制之後,我曾回到老家,那時妹妹一家人也來美國,所以找不到其他的親戚故舊了,因此後來就不太想再回臺灣。
對於在樹林的童年生活,有一件戰爭時期的事情,讓我印象最深刻。1945年間,美軍對臺灣的轟炸愈來愈頻繁,臺北也不例外。大規模的空襲之下,各地損失慘重。記得有一次美軍在臺北進行轟炸時,橫跨在大漢溪的鐵路橋樑上,剛好一部貨車經過,所以軍機就開始俯衝進行空對地的掃射。這時剛好還有另一架也準備攻擊,結果不知何故,前一架爬升時剛好跟俯衝的另一架撞上,兩架飛機就掉落在浮洲仔上面。直到戰爭結束前,飛機殘骸都沒有被移走,聽說飛行員的屍體也沒有被找到。
戰爭一結束,就有兩個美軍來到墜機點附近搜尋。聽說,其中一位美國人會講一點臺語,我猜想那位美國人可能就是George Kerr(葛超智)。[3] 其實,在臺灣有關George Kerr的傳言很多,我聽說他曾建議要轟炸臺灣神社,如此才能打擊日軍士氣,但美國官方可能認為這是文化設施,所以沒有採納這項建議。另外,他還提出轟炸臺北第一中學(戰後改為建國中學),這個建議被軍方採納。聽說,這是因為在1937-1940年間,他曾到該校兼任英文老師,由於當時受到日本人欺侮,這樣的建議,可說是他想要進行報復。他跟臺北第一中學日本人教師是否有不愉快的經驗,以及他是否曾建議轟炸該校,我無法確認。但是,記得在我進入建中初中部時,還可以看到建中的部分校舍被炸毀的景象。所以被轟炸是個明確的事實,但無法印證。我對George Kerr很早就非常感興趣,所以當我搬到加州之後,我就經朋友的介紹去柏克萊大學(UC Berkeley)拜訪過他。
二、到康乃爾大學之路
我能夠赴美國留學,有一段很特殊的因緣。首先,我申請學校並非依照一般程序,而是獲得一位貴人的幫忙,才取得入學許可。這位貴人就是知名的武雅士(Arthur P. Wolf),[4] 我們是在很特殊的機緣下認識。當年他還是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博士生的時候,就到板橋的溪州、沙崙與樹林一帶進行田野調查,我常看到他到處在村子裡走動。當時,來臺灣的洋人並不多,樹林這個鄉下地方更是難得一見,看到他出現在自己家鄉,就想認識他以便學英文。剛好武雅士租的住處,就是我樹林國小同學林忠輝的學生家長的房子,當時已經回母校任教的林忠輝的姐姐林麗月,就是王世慶先生的太太。我透過林忠輝以及他的學生的介紹之後,與武雅士認識。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武雅士覺得我對他的研究很有幫助。因此,他回國後,在我畢業服兵役期間,就幫我申請到可領取獎學金的康乃爾大學入學許可,然後直接寄到我家來。在此之前都沒告訴我,可能是想要給我一個驚喜。有了入學許可後,又通過教育部的留學考試,原本以為就可以順利到美國留學。但是,沒想到竟然一直無法申請到簽證。
.png)
圖2 黃介山出國留學家人送行合照(1965)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
後來能夠順利取得留美簽證,也是有一段很特別的經過。當初,我不僅是取得Cornell University的入學許可,而且我是拿到scholarship的獎助,比一般留學獎學金還要好。但為何沒辦法獲得簽證呢?我自己也想不出原因。一直到1965年,剛好我的指導教授John Lewis(劉易斯)[5] 來到臺灣,他也很想知道,為何我拿不到簽證?所以就陪著我到美國大使館面談。到大使館後,先獲得同意陪我進去面談。沒想到進去之後,面談官竟然直接說:「教授好,你就是John Lewis教授吧!我是你教過的學生。」Lewis教授很驚訝,沒想到在這裡可以碰到曾上過他的課的學生。
由於這樣的緣故,Lewis教授就直接詢問面談官員,為何我不能拿到簽證?此時,面談的官員才說明,因為先前美國國會議員羅伯・甘迺迪曾質詢,為什麼來美國的留學生不能帶太太出來?這是一種歧視。為此,甘迺迪議員還提案修改法令。結果,法令修改之後,赴美的留學生可以帶太太。但是,給予簽證時,卻被要求提出一定會回國的擔保。因為我的父母已經去世,無人可以保證我畢業後會再回到臺灣,所以才遲遲無法取得簽證。指導教授就問,那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呢?面談官就說:如果有大學請他擔任教師,用聘書來證明我會回國就可以了。因此,我就回到法商學院,請行政系吳英荃主任幫我開一張講師的聘書。他雖然只是系主任,因為是黨務高官,可以馬上下令教務主任發出聘書。拿到這張聘書之後,我才順利取得簽證到美國留學。
我是1965年8月來到Cornell大學留學,當時李登輝跟我同年來,而他的學生黃大洲則是早約半年前來留學。黃大洲幫李登輝找到一間公寓,可以開伙,他很喜歡煮東西請臺灣同學用餐,我也經常去他那裡打擾。當時,我先租房子住在美國人家,一個星期10美元,沒辦法開伙,已經吃膩了。知道有李登輝那樣可以開伙的公寓後,就請他幫我找一間,可是已經額滿了。但李さん(李先生)還是不死心,經過他不斷催促,管理員跟他說:只剩下閣樓而已,你要不要。就這樣,我將原本已租半年的房子辦退租,然後搬來跟李さん同住,閣樓的房租較便宜,每週只要8元,而且天天都可去找李さん,生活變得更有趣味。大概在我住進去半年之後,李登輝的太太也來美國,他就搬出去租獨棟的房子。過了不久,我也選擇離開這間閣樓,因為這房子實在太熱了。雖然,後來沒有跟李さん住在同一棟房子,但我們還是經常往來,直到1967年他回國為止。

圖3 黃介山與李登輝、黃大洲合影於康乃爾大學附近住處
(1965.10,黃介山提供)
我到Cornell大學留學,跟隨的Lewis教授是國際政治經濟學者,主要是研究中國,所以我的碩士論文的研究對象就選擇清朝末年設在唐山的「啟新水泥公司」。[6] 依照我的研究的結果,那個公司基本上就是利用特權在營運,所有官僚都分得到一點好處,跟現在中國的國營企業一樣。這實在是很諷刺的事情,我認為百年來的中國社會,根本都沒有任何改變。後來,因為我參與了另一個中國研究團隊,才開始進行臺灣社會的調查工作。他們這群研究團隊有4、5個人,對於中國研究不像哈佛的費正清等人,採取由上而下的研究,探討中國皇權體制,而是採取由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從地方社會著手,進行細部的調查分析。Wolf教授就是採取這種研究方法的代表性研究學者,後來這群人就直接被Stanford大學高薪挖角。結果,這群中國研究團隊整個移到這裡,我也就自然地跟著到這裡來。當時我們的計畫是要研究二十年,所以也不會有必須回臺灣的事情。因為不擔心居留問題,沒有顧忌之後,當然就可以全力參與臺灣人團體的活動。我是1969年來到Stanford大學,要搬過來之前,我太太帶著兩個小孩從臺灣出來團聚,隔年我們生下老三,也就是現住在附近的小女兒。
三、在史丹佛大學的研究工作
我在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有正式研究專員的職位,領取很好的薪水,有人質疑我只是碩士畢業而已,怎麼能拿這樣的薪水。其實內行人就知道,我們不是拿大學的薪水,而是我們替學校賺錢。當時,我們的研究團隊拿到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國家科學基金會)支助的研究經費,獎助金一匯進來,其中的百分之四十,就進入Stanford大學的帳戶,成為行政管理費。換句話說,是我們在幫Stanford大學賺錢,而不是向學校伸手領薪水。由於我們的研究主題非常受到矚目,後來還有一家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國立衛生研究院),也要給我們大筆研究經費,而且表明不用繳交研究報告。我們進行的研究,最後當然會盡力寫出好的研究報告,但是得知這麼有利的條件之後,我們決定選擇後者,這樣一來就不必在拿到贊助的經費後,很快地開始為撰寫提交報告而煩惱。可是我們都沒有想到,到了越戰末期,美國學術研究經費短缺,我們的計畫也不得不中途停止,所以這個計畫只持續了十年而已。
這十年間,我們的研究成果非常豐碩。美國跟中國建交後,美國學界選了十本書當「見面禮」要送給中國時,我們的書也列入其中。我們的研究經費是Wolf跟我掛名申請,但是能拿到經費的主要原因是,我就是海山郡出身者,而且懂得日文與中文。當時,我們在大學裡有兩位女士來當助理,每人月薪600元,另外還有一位臺灣來的張鉦錞先生,他是淡水英專畢業,先在美國領事部工作一段時間,才來到舊金山,記得他不是以留學生身分來美國。除了在Stanford大學的研究團隊,其他在樹林地政事務所,我們還有兩位雇員,負責抄寫資料,跟地政事務所一起上班,但這兩人都是領我們的薪水。
我們的團隊建立非常完整的戶口與土地相關的資料庫,可以把地方社會的動態掌握得很清楚。這些都是藉由日本的土地人口調查所建立的豐富資料,才有辦法建立起來,特別是戶政事務所的除戶簿。過去日本在本國與朝鮮,都沒辦法澈底執行這樣的調查工作,只有在殖民地臺灣做到,因為有警察與保甲行政之力,才得以使土地戶口等資料這麼完整保存下來。警察要求人民報戶口,要求嚴格,例如警察在村裡看到一個孕婦,過了一段時間肚子消下去了,馬上會查看村裡是否有人報出生。相對地,在日本就沒要求這麼嚴,而韓國雖然也有要求,但人民比較會反抗,所以臺灣的資料最完整。我們建立的家族史檔案非常可觀,大概共有三萬人左右的基本資料,最少也可以寫三本博士論文。我還讀清代文獻,日本人的調查報告等。例如岡松參太郎的報告書,我全都讀過了。還有資料彙編等書,有時還要看清代的資料彙編。透過這樣的資料庫,我們詳細地分析漢人社會的家族組織,也了解到地方社會的民眾生活。
我知道把臺灣地方社會的研究拿來代替中國研究,曾經受到一些人的批判。這是冷戰時期被包裝起來的問題,我們的研究並沒有受到這方面的影響。有一位灣區的朋友洪基隆,他曾批評Wolf等美國人類學者,認為他們不該用中國來包裝臺灣研究,而且也沒有真正了解臺灣。其實,這麼批評的人才是缺乏知識,不了解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我們是透過這些研究方法,才得以確實地描繪出臺灣宗族組織的面貌。後來我與Wolf合著出版的專書,成為漢人社會研究的經典名著,廣泛被學術界引用。[7] 臺灣有位研究者曾秋美,主要研究南崁地區的「媳婦仔」,她曾引用我們的著作,後來她出版的書我也有買。[8]
我聽說Wolf與我合著的這本書在臺灣常被影印店盜印,過去這個問題根本沒辦法追究,現在應該有改善了吧!我們的研究除了利用除戶簿,研究樹林地區的家族組織之外,接著是利用地籍資料,進行整個地方社會變遷的研究。可惜等到越戰結束後,所有外部的經費補助大多被終止,大批資料沒有後續整理,整個研究計畫就停止了。這批研究資料應該還在史丹佛大學內吧!只是不知道放在哪裡?因為這樣,到1978年的時候,我們在史丹佛大學的計畫就大致結束了,我也不得不開始想辦法試著到外面找其他的出路。
四、參與舊金山灣區臺灣人社團活動
有關灣區的臺灣人社團,我都是最早的成員,包括教會、協志會與同鄉聯合會、臺獨聯盟三者都有參加。臺獨聯盟的聚會常在我家舉行,我在 Cornell 大學就已經加入聯盟,是一位在那裡從事博士後研究的張先生邀請加入的,因為參與研究團隊工作已經確定,我覺得沒什麼居留簽證問題的顧忌,就直接加入了。加入臺獨聯盟以後,有一位法商學院畢業來美的朋友,常來找我討論,他經常寫信回臺灣,宣傳臺獨聯盟的政治理念。來到舊金山灣區這裡後,經常碰到的是黃呈嘉先生,他在刺蔣案之後,曾賣房子保釋黃文雄與鄭自才。由於他有比較激進的主張,對獨盟的主流派的作法很不滿,常叫我要小心一點,告誡我不要介太深。灣區的臺語教會我也很早就參加了,這裡有一位林彥光長老,他對教會事務很熟悉,你可以去問他。[9] 有關協志會部分,石清正先生比較清楚。[10] 大部分都是石先生要辦什麼活動,交代我負責的我就去做,我對那些細節不太記得,很多事務性的工作也處理不來。
剛才說過,我在史丹佛的團隊能夠擔任重要工作,主要是我會中文與日文。照理說,我日本時代才讀到小學四年級,日文根本沒什麼程度可言。實際上,我的日文能力,是在1945年日本人離開臺灣之後,靠著自己不斷努力地自修而學來的。1947年起,我通車到臺北,常到臺北車站附近的舊書店買書,持續地讀了很多日本人留下來的書。我學習英文的主要方法,也是讀日本出版的英文教材或介紹英美文化的書。透過這樣的課外學習,讓我增進不少新知識,同時也增強我的英文與日文的語言能力。由於我有日文閱讀能力,因此我也閱讀後來在日本出版的王育德與史明的著作。其中王育德《臺灣:苦悶的歷史》這本書,是李登輝拿到博士學位要回臺灣之前送給我的。我想可能是王育德送給他的吧!他回去時當然不敢帶回臺灣,所以才送給我。[11] 另外,到史丹佛大學之後,我知道史明發行《獨立臺灣》雜誌,所以就寫信給史明,請他們把現存的過期雜誌都寄過來給我,有時我也會捐款。
我很早就知道史明寫過《臺灣人四百年史》這本書,自己買了日文版來讀,然後也向石清正介紹過這本書,記得也曾經向他建議,可以將這本書翻譯為漢文版。後來他們集資協助出版四百年史的漢文版,是否有受到我的影響就不知道了。他們集資出版四百年史的時候,可能認為我的財力比較不夠,所以就沒有找我出錢,只找那些從事科技業工作的高收入臺灣同鄉募款。我對臺灣研究相關的英文書也很關心,例如:George Kerr《被出賣的臺灣》,當時聽說很難買得到,我是在史丹佛大學的書籍部訂購買到的,好像不到十美元而已。後來,我去請他簽名,他寫上1970年5月30日──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an “Memorial Day”)。
原本我不知道,簽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是什麼意思。前幾年,我看到張寬敏醫師在《中國時報》發表一篇文章,才知道這是指5月31日的臺北大轟炸,舊金山跟臺北接近一天的時差。所以,我想他所指的應該就是大轟炸這件事吧!
如果那時候我有多一點臺灣歷史的知識,我一定會多請教他。大家都知道,George Kerr戰後停留在臺灣的時候,收集了很
多臺灣相關的資料。聽說,有一次他碰到有人要把一整車的舊書與資料運到郊外當廢紙賣,他把它搶救下來,而且還告訴那個人說,以後有這樣的東西先拿來賣給他。人講「山豬毋捌食過米糠」,這些阿山竟然不知道要接收這些重要文獻,這就是當時臺灣一個很大的問題。George Kerr收集的資料部分捐給他任教過的Stanford大學與Berkeley大學,部分賣給住在西雅圖的臺灣人蕭成美醫生,蕭醫師是他臺北高等學校的學生。聽說他們買他的資料,除了已經可以認定確實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之外,同時也是為了幫他籌款養老。[12]
有關灣區的臺灣人教會活動,我一開始就有參與,從張瑞雄牧師在這裡牧會的時代,我就固定去參加。1975年,灣區臺灣基督教會正式成立,我是最早的成員,灣區教會曾派我參加北美臺灣基督教協會,我也曾經當代表去開會。1980年,在南灣另外設立「迦南臺灣基督教會」,我就改參加這邊的教會。有關南灣成立迦南臺灣基督教會的經過,林彥光與林典謨兩位長老比較清楚,你可以去問他們。我在灣區參加很多團體,主要都是提供意見而已,較少參與實際上的事務性工作。例如,石清正先生財力較好,我就建議他買臺灣文獻委員會全套的《臺灣省通志》,還有整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的「臺灣文獻叢刊」。後來,大家組織讀書會就是分配讀這些書。灣區就讀人文社會科學的人才比較少,所以我才有機會多提一些意見。
五、負責台灣之音電話錄音廣播
灣區的「台灣之音」本來是轉播紐約「台灣之音」的錄音帶,但是聽了一段時間後,很多人說應該要播送本地消息,所以後來才由我來負責籌備設立。我是從1979年4月1日開始錄音播送,到1982年底才結束。結束的原因之一,是我太太得了癌症,我想要轉給別人繼續辦,但是沒人願意接。那個時候,雖然有陳隆來幫忙,但是他也無法接下來。1982年初,紐約台灣之音要收起來時,曾經推薦大家可以繼續收聽灣區的台灣之音,但結果我們也無法再持續下去,只播送到年底就整個結束掉,隔年我太太也過世了。回想起來,台灣之音確實獲得很多人鼓勵支援,但是捐款與財力還是不足。所以,錄音帶必須重複地使用,這樣很快就會損壞,要再買新的。在這種情況下,哪有可能把錄音帶保存下來。因此,當時到底錄製過什麼樣的消息,現在只能看我的手稿了。
灣區的台灣之音能夠獲得大家熱烈的反應,有幾個偶然的因素。首先,高雄事件的播送最重要。因為我跟艾琳達原本就認識,所以開播以後,就曾打電話跟艾琳達聯絡上,有時候我也會打電話去詢問臺灣的最新消息。[13] 高雄事件發生時,我剛好打電話到高雄,知道在高雄發生衝突事情之後,我馬上換錄音帶,有聽眾聽到發生警察鎮壓民眾的情況,馬上就打回臺灣探聽。但是,臺灣的親友卻說:哪有這款代誌!你的消息從哪裡來的。幾天後,臺灣的新聞才正式播報高雄事件,印證灣區台灣之音播報的消息。這件事情傳開來之後,大家才更肯定灣區台灣之音的厲害。
另外,還有一件事也讓台灣之音更加獲得信賴。那時,國民黨開始抓人,但是到底有多少會被起訴判刑,大家議論紛紛,當時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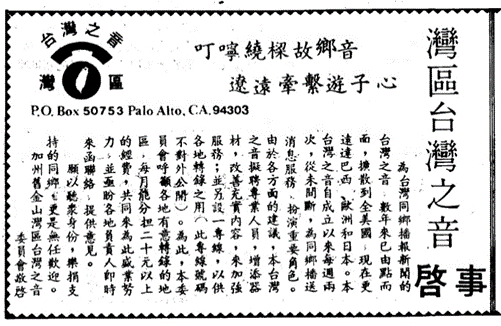
圖5 灣區台灣之音啟事
資料來源:《臺灣公論報》,1982年1月19日,版10。

圖6 灣區台灣之音主持人使用的名片(2017.6.30,何義麟攝)
猜可能會有八人被抓起來重判,結果確實猜對了,八名被移送軍事法庭審判。我在廣播中稱他們為「八傑」,這個相關新聞的播報,也是台灣之音獲得肯定的原因之一。台灣之音都是用臺語播送,我在樹林教會就有學過用羅馬字寫的白話字,原本我就會用比較典雅的臺語,所以用臺語來錄音播送不會有問題。我還曾經在史丹佛大學教一年臺語,這算是一段很特殊的經歷。
史丹佛大學原本沒有臺語課程,當時有幾個學生預定要到臺灣,當時在讀碩士班的艾琳達知道這件事之後,就告訴這些同學,要到臺灣一定要學臺語。因此,這群學生就向學校要求開臺語課。艾琳達的想法,可能是認為可以請她前夫陳嘉勝來教臺語,沒想到她先生表示他不會教,然後就打電話要我去替他授課。記得那班學生共有七個女生,採用美國人學臺語的教材。因為我會讀寫教會白話字,就用這套東西教她們,這些學生暑假去臺灣,發現確實很好用。我記得在康乃爾大學,學校曾經開設過客語的課程。那個年代,在史丹佛大學開臺語課,大概也只有這一次。沒想到消息竟然傳開,隔年夏威夷大學鄭良偉教授就來這裡拜訪我,問我如何教臺語,並送我臺語教科書。
台灣之音的廣播稿都是我自己寫的,因為當時Wolf教授的研究計畫剛結束,但我還是每天到圖書館,還在撰寫研究相關的報告。另一方面,為了要播報臺灣的消息,在圖書館閱讀各種中、英、日文報紙雜誌的時候,也會同時記錄臺灣相關消息的要點,這樣就成為廣播稿重要的來源之一。剛剛開始的時候,負責台灣之音只是副業,沒想到高雄事件發生後,投入的時間越來越多,每次六分鐘、每週兩次的廣播稿,大概就要投入整個禮拜的時間撰稿,根本沒有空閒的時間。這樣一來,撰稿錄製台灣之音,就自然變成我的本業了。
當時,聽眾的反應很熱烈,不斷打進來聽,錄音帶耗損得很快,所以經常更換新的錄音帶。你說1982年初台灣之音的營運委員會有登廣告,曾經表示要擴大服務,這件事情我記不太清楚。整個台灣之音的播送,從撰寫播音稿,到實際錄音、更換錄音帶等等,都是我一個人包辦。到目前為止,很多人來我這裡,都會談到有關台灣之音的事情,但是從沒有人詢問是否有廣播稿的事情,你是第一個問我的。原本我就已經把所有的手稿都整理好了,這是想要留下來做紀念,沒有想到過其他的用途。
六、現在的生活與心境
1982年底結束台灣之音的工作之後,我也開始找工作,最初先去陳文雄(Winston Chen)開設的電子公司Solectron上班。[14] 後來,自己也開公司,我的公司Eveready Industry Corp. 也是一家電子公司,經營得還算很順利。1983年,太太過世後我再婚,新妻名叫謝淑玉,北一女畢業來美國,在Utah(猶他)州的Salt Lake City(鹽湖城)的一所大學進修。婚後她讓我全力投入新的事業,經濟上還算寬裕。1991年買了目前Palo Atlo住的這間房子,退休之後一直住在這裡。目前子女都已長大,小女兒就住在附近,隨時可以過來看我跟我太太,生活得很平順。
很可惜,我的小孩也都不會說臺語了,美語才是他們生活的語言。我主持台灣之音之前,可能就被列入黑名單,所以長期無法回到臺灣。直到1992年,相隔27年之後,才能夠回去樹林,探望親友。那時看到臺灣的情況,都跟以前不太一樣了,目前已經沒有什麼親戚在臺灣,所以也沒有再回去的打算。現在每星期上教堂之外,也跟灣區的臺灣同鄉保持聯繫,臺灣的事情當然也很關心,但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我只希望臺灣未來能有更好的發展。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1] 根據臺北師範學校學籍資料顯示,黃元是1930年從臺北第二師範學校畢業。檢索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可知:他在1931年擔任龍山公學校訓導,隔年就轉到板橋公學校任教。另外,黃元的妹妹黃氏寶貴,1940年起成為「教員心得」(代課老師),任教於樹林公學校。根據黃介山說明,1945年戰爭結束前幾天,黃寶貴因病去世。
[2] 孫理蓮(Lillian Dickson,1901-1983),生於美國明尼蘇達州彼略湖城,財團法人基督教芥菜種會的創辦人之一和牧師孫雅各的妻子。她跟隨孫雅各牧師來到臺灣,積極投入宣教事業,特別關注原住民宣教事業。請參閱:李貞德,〈從師母到女宣:孫理蓮在戰後臺灣的醫療宣道經驗〉,《新史學》16:2(2005.6),頁95-156。
[3] George Kerr(1911-1992),正式使用中文名:葛超智,一般譯為柯喬治、喬治‧柯爾,生於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1935年到日本求學,1937-1940年間擔任臺北高等學校英文教師,可能也因此兼任臺北第一中學教師。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進入美國戰爭部戰略情報局工作。戰後擔任美國駐臺領事館副領事,對二二八事件有深入了解。1965年,他發表Formosa Betrayed一書,中譯:《被出賣的臺灣》,嚴厲批判國民黨政府,因而受到臺灣各界的矚目。
[4] 武雅士(Arthur P. Wolf, 1932-2016),以臺灣為田野的美國人類學學者,史丹佛大學教授,有關武雅士與臺灣的因緣,參見:〈第六章 武雅士夫婦及其報導人〉,周婉窈,《臺灣史開拓者:王世慶先生的人生之路》(臺北:新北市政府文化局,2011),頁77-85。
[5] 劉易斯(John W. Lewis, PhD,1930-2017),國際政治學者,也是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史丹佛大學政治學教授。
[6] 根據「維基百科」:啟新水泥公司在1889年創立,是中國第一家近代水泥公司,原名「唐山細棉土工廠」,1906年改為官督商辦企業,名為「啟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工廠位於唐山市,總部在天津。1954年更名為「唐山啟新水泥有限公司」,黃介山的研究涵蓋到戰後的經營情況。
[7] 黃介山與Wolf 的研究著作:Arthur P. Wolf & Chieh-shan Huang, 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 1845-194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8] 曾秋美,《臺灣媳婦仔的生活世界》(臺北:玉山社,1998);曾秋美,〈南崁媳婦仔習俗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9] 有關灣區臺灣基督教會,參見:何義麟,〈美國舊金山灣區臺灣基督教會史料簡介:以社教暨建堂紀念特刊為中心〉,《臺灣史料研究》53(2019.6),頁25-69。
[10] 有關臺灣協志會,參見:何義麟,〈臺灣協志會石清正先生口述訪談紀錄〉,《臺灣風物》67:2(2017.6),頁133-170。
[11] 王育徳,《台湾:苦悶するその歴史》(東京:弘文堂,1964)。從出版時間與李登輝赴美時間來看,王育德有可能贈送此書給李登輝,但細節尚待確認。
[12] 蕭成美醫生購買部分George Kerr收集的文獻資料,目前收藏於臺北二二八紀念館。部分資料已經整理出版。
[13] 有關艾琳達在史丹佛大學與參與灣區臺灣人社團的情況,參見:艾琳達口述、林佳瑩著,《美麗的探險:艾琳達的一生》(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2011)。艾琳達接受筆者訪問表示,黃介山是Wolf的工作伙伴,自己是被Wolf逐出師門的學生,兩人是熟識的朋友,但高雄事件前後,並未與黃介山直接聯繫上。
[14] 有關陳文雄的創業故事,參見:川上桃子,〈第6回 シリコンバレーの「無名の巨人」ソレクトロンを率いた臺湾人経営者Winston Chen氏の歩み〉,《アジ研雑誌記事 / IDE Article》,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アジア経済研究所發行網路刊物/Institute of Devel- oping Economies,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IDE- JETRO), http://www.ide.go.jp。
Source from 何義麟
Posted in 08/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