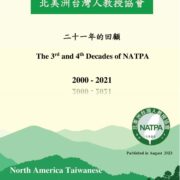懷念林宗光
作者 楊遠薰
林宗光教授
林宗光去世已一年多,不久前,他的太太唐錦慧打電話給我,聊了些往日舊事與她夢見林宗光的情境。一時,林宗光講話帶笑的神情猶在眼前,令人十分懷念。
林宗光是位公眾人物,也是個很可親的朋友。眾人知道的他是前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會長、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暨前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博士的公子。私底下的他是個活潑、風趣與隨和的人,很照顧年輕的一輩。我們於八十年代在愛荷華相識,前後相處七年,如今回想當年的情況,許多溫馨的感覺不禁湧上心頭。
1
林宗光是個親和性很強的人。1980年四月,阿加應聘到愛荷華州立大學食科系擔任助教授(Assist Professor),我們遂搬到愛荷華州的艾姆斯城 (Ames, Iowa)。阿加到系裡上班數日後,有位學生告訴他,星期五晚上若到愛大的體育館打球,會看到一些台灣學生與同鄉。阿加邀我前往,我們果然在籃球場邊看到幾個黑頭髮的人。
不久,有個人過來和我們打招呼,自我介紹說他林叫宗光,在迪莫伊市(Des Moines)的德雷克大學(Drake University)教書,每星期五晚上都帶三個兒子到愛大打球。他親切地問我們在哪系就讀或工作?叫什麼名字?還說下星期若天氣暖和,他們將移師戶外打壘球,歡迎阿加加入,也歡迎我去觀球。隨後,我們互換電話號碼後便告別。
所以第二次見到林宗光,是在愛大的壘球場邊。阿加與他們一起練球,懷著身孕的我在球場邊觀看。但見一群大男生馳聘球場,又吼又叫,遇漏接或打壞球時,還會沮喪地擲球套,看來很認真。
打完球後,眾人聚在球場邊喝水,並向我與阿加問這問那。他們問我們住哪兒?我說:「不遠,就在大學西邊的住宅區,歡迎大家到我們家坐。」結果此話一出,他們七嘴八舌一下,竟說聲:「好,走!」然後各自開車,隨我們的車到我家。
那日一進家門,我連忙鑽進廚房張羅茶水,待端到客廳,見一群人或坐或站,高聲談笑,歡喜自如,不禁啞然失笑。後來方知星期五晚上是他們的快樂時光,打完球後,通常到某個人家吃些水果,聊一陣天後再回家。
Iowa壘球隊部分隊員合影。前排左一為隊長林宗光,中為許學加
不久,一位叫張淑媛的太太打電話給我,邀我們參加艾城台灣同鄉會的端午節聚餐。就在那餐會裡,我們見到林宗光的太太唐錦慧,也認識了在艾城工作的幾戶同鄉包括在愛大執教的蔡玉銘教授夫婦、陳慶昌教授夫婦、黃樹民教授夫婦、服務美國農業部的黃文源博士夫婦、任職私人公司的黃藻芬博士夫婦,就讀物理系博士班的林茂清夫婦…等等。這些人後來都成了我們的好朋友。
其時,同鄉會的人稱呼對方都連名帶姓地叫,從不加教授、醫師、博士…等頭銜。我入境隨俗,亦喊林宗光的名字。孰知他似認真似開玩笑地對我說:「妳要喊我『阿公』,因為我的名字就叫『阿光』。」
我一時不知如何回應,幸好旁邊立刻有人代答:「你是阿公,那我就是阿祖哩。」
「嘿,你是自稱的阿祖,我可是真正的『恁祖公』(林宗光) !」他亦不甘示弱地回道。
這時,眾人都笑成一團。那是我到美國的第三年,在這之前兩年,大抵生活在美國人圈裡,對於一到艾城能很快地認識到這麼多同鄉,與大家毫無拘束地笑談,覺得很快樂。不知不覺地,我對同鄉會有了歸屬感。
2
林宗光有個特殊的家庭背景,也有個好太太。初識唐錦慧,覺得她性情溫婉、看來就是個賢妻良母型的人。她與我話家常,說她的小名叫Suzu,在一家銀行工作,與林宗光是東海大學政治系的同班同學。他們留學美國的第一年,就在加州結婚,然後搬到波士頓。林宗光在塔夫特斯(Tufts)大學Fletcher法律外交學院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她一連生了三個兒子,在家相夫教子。1970年,林宗光應聘到德雷克大學教書,他們乃搬到迪莫伊市…,聽來就是個美麗的「班對」的故事。
唐錦慧 (Suzu)
不久,一位同鄉告訴我,林宗光的父親是前台大文學院長暨二二八事件受難人林茂生博士,唐錦慧則是往昔鼎鼎有名的高雄唐榮鐵工廠的唐家小姐。我聽後「哦!」地應了一聲,心想若在台灣,人家是名門之後,大概不會與我們在一起,但在台灣人很少的愛荷華,他們不但熱誠地招呼新來的人,還與大家一起搬桌搬椅地辦同鄉會,豈不令人窩心?
事實上,林宗光與Suzu待客之熱忱,確實會讓人感到很溫馨。我始終記得1980年聖誕節前的一個週六到林家造訪的經過。
那時,產後的我一直居家照顧娃娃,很想出去走走。阿加乃趁週末,帶我們到都城迪莫伊市看聖誕節的光景。出門前,我打個電話給Suzu,說我們要到她家附近的購物廣場逛街。她馬上說:「逛完街後,請到我家坐。」
於是那日午後三時許,我們抱著四個月大的女兒抵達林家。林宗光夫婦不僅陪我們聊天,還逗小娃娃玩。林宗光尤其一直抱著baby,直誇她可愛,還說他只要抱女生,不抱男生,讓我想起他們家有個「男孩是草、女孩是寶」的傳聞,便問起這事。
林宗光因此繪聲繪影地把他媽媽一連生了八個兒子,直到第九胎才生個女兒的故事說了一遍。故事的精彩處是街坊鄰居聽到他生了個女兒,都替他父母高興地舉雙手喊「萬歲!」
我笑問林宗光:「你出生時,有沒有人喊萬歲?」
「沒有,」他故意蹙著眉,搖頭道:「我是第十個孩子,又是個男生,沒什麼好慶祝的。」
我們如此笑談著,不知不覺竟已天黑。愛荷華的冬天天黑得早,那時不過四點多,但Suzu說:「天黑了,吃個晚飯再回去吧。」說著,便走進廚房,開始動鍋鏟,林宗光也開始擺碗筷,同時一再留我們吃飯。我們於是厚顏地在林家享用一頓美味的晚餐。
餐畢,我們隨即告辭。林宗光送客到門外,一見外頭曾幾何時竟已由下雨變成下冰,立刻叫起來:「啊,下冰了,你們趕快回屋去!今晚在這裡過夜,明天再走!」
「不行,我們得回家。」我說。
「不可以,下冰天開車最危險,趕快回屋去!」他又叫道。
我們以沒帶足夠嬰兒東西為由,堅持上路,結果那晚幾幾乎乎回不到家。
因為整個大地全結上一層冰,高速公路亦然,讓我們真正體會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驚險滋味。當時,所有的車子都減至最低速,難以駕控地扭曲蛇行。開車的人固然開得心驚膽跳,坐在旁邊的人亦摒息不敢出聲。結果,平時一小時的車程那晚整整開了八個小時,當夜半三更安抵家門時,阿加與我都鬆了一口氣。
後來每逢下冰,我就想起當年的驚險之旅,也連帶記起林宗光夫婦對我們的熱誠照顧。
3
八十年代的愛荷華州大台灣學生圈裡,其實籠罩著一層詭譎的氣氛。
起初,我們單純地請幾個台灣學生到家裡吃飯,但他們似乎不那麼融洽。後來有學生告訴我,我請的人裡有位據傳會打小報告的仁兄,與之講話要當心。
所以下回再請學生吃飯時,我不再請那位仁兄,餐桌上的氣氛果然好轉。他們告訴我:高雄事件發生後,愛大的K黨活躍份子立刻打電報回台灣,譴責「暴民」,並在愛大發起捐款給受傷員警的運動。不少人都捐了錢,但隨著國民黨政府大舉逮捕異議人士的消息傳出後,便選擇沉默。
在與這些學生較熟後,我請他們參加台灣同鄉會。他們卻面帶難色地說:「台灣同鄉會裡有左派,也有台獨。參加台灣同鄉會,會被列入黑名單。」
他們口中的左派係指其時執教愛大、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人類研究所所長的黃樹民教授,台獨乃指林宗光教授。
我說:「他們都是很好的人呢!何況參加同鄉會,不過一起吃個飯,哪會這麼嚴重?」
「會喔!」他們很認真地回答:「愛大真的有國民黨特務,妳和許老師都要小心哦。」
隔(1981)年七月,執教匹茲堡大學的陳文成教授返台探親,被警總約談後陳屍台大校園的命案發生,在在顯示國民黨的校園特務確實活躍於美國各大學,大家心頭都籠罩一層烏雲 。
在這氛圍下,台灣同鄉會不易招募到新人,像我們這種願意參加的得自然到前輩們的諸多照顧,時常被邀請到同鄉家裡吃飯。
1981年確是多事之年。美麗島事件正在審判中,林義雄家滅門血案與陳文成命案接踵發生。這些事件像炸彈般震撼每個人的心,餐桌上的討論因此熱烈異常。大家屢屢談得慷慨激昂、義憤填膺。
我這時也比較明白林宗光每星期開老遠的車到艾城打球的原因。
林宗光與唐錦慧伉儷
林宗光心裡想必有一個想要引導年輕一輩瞭解歷史與事實真相的使命感,但他所執教的德雷克大學係私立人文大學,沒有台灣學生,所居住的迪莫伊市又甚少台灣人,因此利用每週末到愛大打球的機會,接近新來的台灣學生、年輕的教職員與博士後研究員,招呼他們,引導他們參加台灣同鄉會、進而認同台灣,可謂用心良苦。
於是逐漸地, 我們發展出一種由同鄉輪流作東、私下邀請學生參加的pot luck聚會,也就是每家準備一大道好菜,眾人一起大快朵頤。結果這個幾乎每月一次的家庭聚會成了我在愛荷華最鮮明的記憶。
那時參加聚會的約大人二十多位,小孩十餘位,一屋子熱鬧騰騰。林宗光夫婦與許宗邦夫婦每次都自迪莫伊市趕來與會。許宗邦與陳秀芬是一對晚我們一年到愛荷華的的年輕夫婦。 他們的年紀小我們一、兩歲,兒子與我們的女兒同齡。許宗邦當時在迪莫伊市的一家醫院擔任住院醫師,亦在愛大的體育館認識林宗光,接著受到溫情感召而被網入台灣同鄉會,因此與我們結緣。
當年大家皆處於三、四十歲的壯年,個個食量大、胃口佳,吃起飯來如秋風掃落葉。聚餐時每見滿桌佳餚,但眾人輪流拿過一、兩回菜後,便盤底朝天。我們這些家庭煮婦見大家如此捧場,菜不僅越做越色香,份量也越大份,結果個個都成為廚藝高超的好廚娘。
記得輪到在我家聚餐時,我常多煮一鍋酸辣湯。那鍋子大得如從前在台灣燒洗澡水的大鍋,作料與湯放到七分滿。因為太重,那鍋湯一直放在灶上,由喝湯的人自己搖。記憶裡,林宗光常穿著便裝或運動服,站在廚房中央,一邊喝湯,一邊神采飛揚地與週遭的人談話。
他講得多,也吃得多,時常喝了一碗湯後,又去搖第二碗,同時不吝讚美道:「這湯真好喝,真夠味!」他說話時,眉眼帶笑,意興風發,表情十分生動。
為什麼我會有這印象?因為那時吃飯,小孩與太太們先拿菜,先生們就聚在廚房先喝湯。林宗光的消息來源多,在大學裡又教歷史,講話有幹有枝、有始有末,所以大家喜歡聽他講,也樂於發表意見,所以一屋子都是話聲。
那時的餐會往往從傍晚六點開始。眾人喝湯時開講,拿了菜、坐在餐桌時繼續講。餐畢,坐在客廳沙發,又邊喝茶、邊聊天、也邊吃點心,總得聊到半夜、孩子們都東倒西歪地睡著了,才各自領了睡眼惺忪的孩子們回家。如此月月年年,一些深厚的情誼就不知不覺地累積。
至於為什麼林宗光常穿運動服或便裝?因為他每星期六從早到晚都帶著三個兒子到處趴趴走。他喜愛音樂,通曉名曲,更熱衷運動,歡喜包辦三個兒子的課外活動。每週六一早,他帶孩子們去學琴,下午一起去釣魚或打球,傍晚則直接開車到聚餐處吃飯。全職上班的Suzu每每利用週末洗衣、買菜、做菜…,然後載著一大鍋熱騰騰的菜,到聚餐處與他們會合。
林宗光與他的三個兒子
也因此,我們都目睹林宗光與三個兒子像父子、像兄弟、也像朋友般地同進同出,也望著Hoyt, Ian 與Jimmy三兄弟由可愛的少年逐漸成長為英俊的青年。
我有時想:林宗光如此用心且歡喜地當個好爸爸,是不是與他年少失怙、缺乏父愛的遺憾有關?他的父親林茂生博士畢業東京帝大,是第一位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的台灣人, 1947年任台大文學院長時,228事件發生,無緣無故地被逮捕,此後不復還。
林宗光說,當年身為老么的他年僅七歲,渾然不解世事,爾後迷迷糊糊地長大,直到成人,才從文獻裡認識自己的父親,自是悲慟萬分。
228事件過去於我是樁隱晦的歷史,認識林宗光後,方知這是一個多麼沒有人性、戕害百姓的事件,對受難者家屬的打擊何其殘酷!設身處境地從受難者家屬立場看,林宗光想要昭示歷史真相、甚至控訴國民黨政權不公不義 的心境自可理解 。
4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於1980年在芝加哥成立。林宗光的學識、才能、親和力與家庭背景使他很快地在教授協會受到矚目。
他與NATPA早期的會長如廖述宗、蔡嘉寅、吳得民等教授皆熟,與稍後活躍於NATPA的陳文彥、賴義雄等教授更有同窗好友的情誼,所以他很自然地投入該會的事務,並順理成章地在1986年出任NATPA總會會長。
1984年時的林宗光教授
然因愛荷華地處內陸,距台灣人聚集的大城皆遠,所以林宗光常獨自飛東、西兩岸,參加NATPA 的會議。倒是我們在愛荷華的那些年,曾數度與他及Suzu 開車到堪薩斯城,參加平原區NATPA年會與台灣人秋令營,留下一些美好的回憶。
記得當時自迪莫伊市或艾姆斯城開車到堪薩斯市,約需六、七小時,當天無法往返。我們因為在堪薩斯有親人,可藉開會之便探親,所以通常自愛荷華前去的,只有林宗光與我們兩家。
林宗光頗有大哥之風,一起出去開會,都很照顧我們,所以當時我們與平原區的一些教授如黃金來、吳得民、周式毅…等皆熟。1984年,林宗光主辦平原區NATPA年會時,即假愛荷華州立大學的會館舉行,當晚則在吾家小屋進行聯誼party,算是我們與NATPA的一段情緣。
我們於1987年離開愛荷華,搬到紐澤西,此後與愛荷華同鄉見面的機會日益減少。然而縱使分離二、三十年,我們依舊保持聯絡,每年聖誕節都會收到對方親筆寫的賀卡或問候電話。每次電話一聊,話題一個接一個,就像從前開home趴般,講個沒完。
此外,我們也曾數度與林宗光夫婦相見 。我們住紐澤西時,他們曾到我家。我們邀請了林宗光的姐姐林詠梅、姐夫徐福棟及曾在愛荷華州大求學的林茂清、翁玉屛一起聚餐言歡,共度一個美好的晚上。
由左至右:徐福棟博士、林詠梅與唐錦慧合影於九十年代
我們也曾在美東夏令會及其他場合遇到林宗光與Suzu。每次,我們都盡量坐一起,面對面地吃餐飯,互報近況。
大約2006年,我住巴爾的摩時,有次趕到華府採訪一個有關美、中、台關係研討會的新聞。匆匆進會場後不久,聽見有人喊我的名字,回頭一看,我不禁驚叫起來:「啊,林宗光,你怎會在這裡?什麼時候來的?」
「我今天上午到。」他微笑道:「他們找我來講幾句話。」
研討會很快地開始,他果然坐在台上講員的位子。我從台下望著他,不知怎地,竟覺有些陌生。直到他開口講話,那聲音、語調與臉上的表情一如往昔,過去那種熟稔的感覺才又攏上心頭。
研討會結束後,我走到他面前,低聲問他:「你有沒有空?要不要到巴爾的摩玩?或讓我們請你吃個飯?」
「這次恐怕不行,」他語帶歉意地說:「下次好嗎?我快退休了。等退休後,我會偕Suzu到華府看朋友,屆時一定通知你們。」
我環顧周遭,見一些台派大老都圍在他身邊,便說:「好,那我回去了,下回見。」
「呀,請向阿加問好,下回見。」他說。
但人生有時就沒有「下回」,那次是我與林宗光最後一次的見面。他與Suzu後來雖曾兩度到華府,也都通知我,但我都在台灣。
其後,我常從秀芬處聽到林宗光夫婦的消息。陳秀芬與許宗邦早我們一步離開愛荷華,搬到南加州。我後來若到南加州,都去投靠他們。秀芬說,林宗光每次到南加州,也都住他們家。所以秀芬常居中傳遞消息,譬如他們兩家何時到何地旅遊…等等。
有一天,秀芬在電話中憂心地告訴我:林宗光得到癌症,而且一發現,就是末期。
我心頭一驚,連忙打電話給林宗光。當我嚅嚅地向說聽到他生病、阿加與我非常難過時,林宗光卻神清氣爽地回道:「不要難過。我的手術很順利,復原的情況很好。」
然後,他將如何發現得病與治療的經過詳細敘述一遍。他的口氣依舊爽朗,講話仍然有力,很難想像一個面臨生命烏雲的人會有如此氣定神閒的功夫。
正因為他的個性樂觀,林宗光最後幾年依舊活得瀟灑自如。他在體力比較恢復後,及偕Suzu與好友到全球各地旅遊,也開車到美東探訪親友。注重天倫之樂的他一直住在距兒孫最多最近的迪莫伊市,在離世前一年,還安排全家三代二十餘人一起回台灣旅遊。喜歡朋友的他亦在最後半年飛到南加州,參加教授協會年會,並在會後的旅遊中擔任Captain,與眾人同樂。
林宗光(最右者)全家2012年回台旅遊大合照
然後有一天,秀芬打電話給我,語氣沉重地說:「林宗光癌症復發,這回恐怕不樂觀。」
我因此又打電話給林宗光,奇妙的是電話那頭依然傳來他一貫歡喜的聲音。他這回大談他們全家回台環島旅遊的經過,我順著他的興致接腔。末了,他還叮嚀我說:「妳也要帶你們全家回台玩一玩,非常值得的。」
「好,一定。」我說。就這樣,直到最後,林宗光依然留給我正面、積極與爽朗的形象。
約三個月後,秀芬飛了一趟愛荷華,與林宗光道別,並陪Suzu數日。我隨後在報上讀到數篇追悼林宗光的文章,卻始終無法平下心來寫他。每一想起林宗光,就憶起初識那年,他甫過四十、阿加未及三十、兩人都英俊瀟灑的模樣。如今斯人已去,我們亦華髮叢生,不免惘然。
如此又過一年多,有天在報上讀到許宗邦出任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總會會長的新聞,我不覺莞爾。猶記初抵愛荷華時,我們都是純正的國民黨教育下長大的青年,後來經過鄉親們的招呼與開導,方有不同的思維與認同。想來前輩們播的種萌了芽,也結了果。
由左至右:許宗邦醫師、黃金來教授與許學加教授合影於1984年平原區NATPA年會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翰福音12:24) 這些日子,我懷念林宗光的笑容與熱情,也想起這段經文,不禁感到曾受前輩照顧的我們亦當如是,應繼續以關心、耐心引導年輕一輩,讓認同台灣的理念不斷傳延下去。
楊遠薰的部落格: http://overseas-tw.blogspot.com/
源自 楊遠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