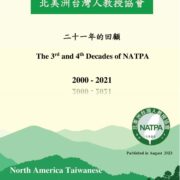力爭上游
作者 張丁蘭
小學快畢業時,班上好幾個男生都要從壯圍鄉下進城到宜蘭考中學。我知道當時壯圍鄉共有四個小學,從來沒有一戶人家會讓女孩子繼續上中學,但是我卻不喜歡留在家裡做家事;正當不知何去何從的時候,學校的校長和導師都到我家去勸我父親讓我去報考試試看,結果我竟吊車尾地考上蘭陽女中,成了壯圍鄉第一位考取蘭陽女中的傳奇女生。但是在興奮之餘,村裡的人也七嘴八舌地議論紛紛,他們都認為讓女孩去宜蘭唸女中,是「無睬錢」的傻事,但是我的父母並不反對我升學。
我的父親還為我買了一部小型24吋的中古腳踏車,好讓小個子的我可以騎車到蘭陽女中上學,否則從我家到學校走路要花一個半鐘頭。每天上學,我得小心翼翼地在鄉下崎嶇不平的道路上騎著腳踏車,更要費力地和濱海的大風雨搏鬥。其實,對我來說,更大的挑戰卻是如何和一大群剛認識的城裡同學相處;我這樣又害羞又自卑的鄉下女生,自己也經常懷疑,到底是否值得花上家裡那麼多錢,換來如此艱苦的求學境遇。
初中第一學期結束時,我的成績祇能勉強過關,畢竟鄉下學生的程度遠比不上城裡學生的程度。初二那年,我被分在最好的班級,在逐漸適應學校環境和同學課業競爭之下,好勝的我,功課漸漸地迎頭趕上。
初中畢業時,我考慮去台北考公費的女子師範學校,一來可以不用讓家人負擔我的學費,再者當時在宜蘭鄉下,一個女孩子能夠當小學老師,已經是讓人又羨慕又尊敬的工作了。
參加女師考試前一天,我第一次乘坐火車到台北城, 那天是父親騎著腳踏車載我到宜蘭火車站,想不到卻在進了車站月台後,才發現准考證放在父親腳踏車上的袋子 裡,但是父親卻已騎車離開了。我望著消逝的父親背影,以及同時駛進月台的火車,不禁失聲痛哭,一路哭著回家。我的小學老師夢想也告吹了。
在家人和歷史老師的安慰與鼓勵下,我決定留在蘭陽女中唸高中。我的成績始終保持五名之內。蘭陽女中的訓導主任一再勸說我去加入國民黨,他愈是說入黨有多大好處,我愈是反感他對年輕學生的利誘。因此,我始終不願入黨。
1950年代的蘭陽女中,曾發生過白色恐怖案,當時學校裡的老師、學生都有人因涉及左傾思想的讀書會或歌詠隊而遭到逮捕。我記得公民老師、體育老師和訓導主任也曾被叫去問話,有的人則是一年後才回來。類似的情形, 也曾發生在我大姐夫身上。
我的大姐夫是個地主,日據時代在警察局當書記,國民黨來台後實施「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政策,將 他的土地都放領光了,大姐夫十分不滿,經常批評政府, 卻被當局以流氓名義要抓他,於是大姐夫祇有逃亡到花蓮一段時間。姐夫逃亡期間,在宜蘭的大姐家中生活很苦,母親也不忍心,常常叫我偷偷地送魚去給大姐,為了不讓鄰人說「女兒仔賊」之類的閒話,我往往要繞到大姐家的田裡進去,好避人耳目,想起來實在悲哀。
蘭陽女中畢業後,我考上了中興大學社會學系,當時整個宜蘭地區,很少有女孩子唸大學,雖然我們那一屆包括我在內,只有五個女生考上大學,卻已經是打破歷年來的紀錄。
我在中興大學時,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為了減輕家裡的經濟負擔,大二那年,我就申請到國際婦女會獎學金。這是為了要培發社會工作人員的獎學金,全台灣只有二個名額,我一直領這份獎學金到大學畢業為止,讓我不用向家裡拿學費。至於生活費方面,我也兼當家教,完全不用向家人伸手。
大二那年父親病逝,正當期考前一個星期,緊跟在後頭二、三名的男生,以為這次他們有機會了,但是我的成績仍然是全班第一名。我修台大教授龍冠海教授的課,做了一篇論文,題目為「鄉村生活習慣的調査」。我吩附二個弟弟協助,完成不少問卷調查。龍教授十分滿意我的論文與調查,經常在校內、校外介紹我的論文,對我有很大的鼓舞。
大學畢業後,我到台大醫學院兒童心理衛生中心工作,為問題兒童做心理輔導,當時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為了援助開發中的國家,也在台灣提供公費留學獎學金,以培訓基層人才。我又順利地獲得這份美援獎學金,到美國留學二年,攻讀社會工作碩士學位。學成後,依規定要回國服務二年。
1962年我隻身到美國波士頓的西蒙斯學院留學,當時到美國的台灣留學生很少,資訊也不發達,我對美國全然無知,一切就只有靠自己摸索學習。我們班裡外國學生只有我和另一位從南美洲來的女生,在陌生的國度裡,我們兩人很快就建立起同病相憐的友誼。只可惜不到三個月,她就受不了思鄉寂寞和功課的壓力,在聖誕節時,即向我借錢跑回家,從此輟學不再回來學校。
當時美國和台灣的生活水準實在差異很大,尤其對我這個鄉下女孩來說,更是出了不少的洋相,鬧了不少笑話。
在台灣時,我從來沒看過的洗髮精,竞然被我誤以為是髮油拿來抹,直到有一天碰到下雨,突然察覺自己頭上竟然猛爆泡沫,才知道不對勁。
我在美國留學時,也吃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狗罐頭。起初,我並沒有特別留意罐頭上的貓、狗圖案,還以為是「狗頭」牌的罐頭:由於美國人不吃動物內臟,就將雞胗、雞心、內臟製造成餵狗餵貓的寵物罐頭,價格十分便宜。過去在台灣,只有在過年過節時才有機會和弟弟搶食內臟:我無意間在一家肉店買到雞胗,以為物美價廉的大發現,於是常買回去學生宿舍,拜託另一位也是從台灣來的護理助理幫我燙熟,再好好享受這麼「俗擱大碗」的美味。要不是有一天,肉店老板問起我這位老主顧:「到底養了幾隻狗?」我可能還不知道自己一直都在和貓、狗搶吃牠們的糧食哩!
第二年,我搬出學生宿舍,到貧民區住,同時從事社區的社會服務工作。起初,我的校長十分擔心我的安全;但是我在上課之餘,每個週末幫助社區黑人小孩,和他們到公園去玩,帶領他們從事團體遊戲,很快地和他們變成好朋友,不但我的住宿不用花錢,每週還有五頓晚餐不用錢,更重要的是讓我學到很多社會關懷工作的實務經驗,對我日後在紐約州政府從事社會福利工作有莫大的幫助。
過去,美國黑人一直受到歧視,時常引發衝突,黑人民權運動的導火線是在1955年12月1日,一位黑人女士Rosa Park從百貨公司工作下班回家時搭乘巴士,很疲倦的她不願遵照巴士公司的陋規讓位給白人坐,巴士司機便強迫她讓位,並叫警察來逮捕她,引發黑人發動抵制這一家歧視黑人的巴士公司;黑人堅持上班用步行、騎腳踏車,或集體分批載運的方式通勤,抵制活動持續381天。馬丁路德•金恩帶領的非暴力黑人民權運動,從此如洶湧急流的河水。
在課堂上,我們也經常討論黑人受到種族歧視的問題。在美國貧民區為黑人小孩提供課餘娛樂團樂活動時, 黑人小孩偶爾也會笑我說不好的英文,但是我覺得他們認為我比較沒有優越感和威脅性,並不會排斥或拒絕我。唸社會學和從事社會工作,讓我原本害羞的個性逐漸變得開朗、大方。








摘自 張丁蘭的故事 20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