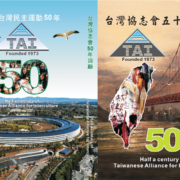一個神經外科翳師忙碌的生活
作者 黃勝雄
其實,我要感謝的病人很多很多,因為有他們才有今天的我。我是從台灣醫學院畢業後,才去美國進修接受訓練養成的一個神經外科醫師。我不是美國的醫學院畢業生,美語也不是我的母語,可以想像在美國社會裡要適應,要出人頭地多困難。想在美國社會上有競爭力,就要格外努力,時時要戰戰兢兢過日子。
一方面需要充實自己,認真閱讀醫學文獻和雜誌,好掌握最新的醫療資訊,另一方面也要參與社交、分擔公共事務的社會責任。在大學教學醫院裡我曾參加外科部的醫師資格審查委員會,我也參加過醫學院的入學委員會。在州級的醫師公會我也曾是他們宗教和倫理委員會的主席,使我在忙碌的臨床工作外又加了更多的重擔和學習的機會。
在專業上我是神經外科專科醫師,也是美國神經外科醫師的徵審委員會(American Board of Neurosurgy)委員。同時也是美國外科學院的院士,不認識我光看這些頭銜最起碼還是會令人心生敬畏的。因為我的專科訓練及謹慎對待病人的細心照顧,使我的同事和神經內科醫師願意轉介病人給我。久了之後,當醫師本人或護士自己變成了病人而需要神經外科的幫助時,他們也會選我擔任他們的主治醫師,真是何等慶幸和光榮!自然這也會增加我無法拒絕的麻煩而不能自拔。有時候感覺能挑病人治療是一種光榮,但每每忙到三更半夜才能回家,想到反而忽略了教育自己的子女而不免懊海!
按美國神經外科學會的統計,我的工作量是平均值的一倍,每年統計要看的病人門診加醫院會診全部加起來有五千六百人次之多。這樣的數目,數十年如一日,就算是鐵打的超人也會有厭倦的一天!雖然工作多,收入也高,但相對沒有生活品質。唯一自傲的是,週日我們全家總會一齊去教堂做禮拜。
一九九三年八月,我決定年底從繁忙的醫療生涯退休,轉換跑道做一個宣教師。我發信給醫師朋友和醫學院的同事,告訴他們我的決定。這封信帶來了兩種反應,在費城醫學院任教的朋友能瞭解,用祝福的心為我在教授俱樂部安排了惜別祝福的餐會並送我珍貴的禮物。另一種反應是在較遠的匹茲堡大學Peter Jannetta教授以為我是受到什麼醫療訴訟的干擾才想退休,竟然提供我另一個研究教職,邀我去參加他在匹茲堡大學的團隊。這使得我不得不去拜訪並謝謝他。
我也另外發送了一封信給我的病人,告訴他們我將結束執業而離去,他們可以來取回他們的病歷或讓我轉送給他們指定的醫師,我這也才發現,過去二十年中,我竟然看過這麼多的病人,有近十萬本的病歷。
在一九九三年十月的一個星期六,我們的美國乾媽約我們去一個鄉村俱樂部聚餐,要我們提早下午四點就去。去了才知道,這是乾媽和病友為我們安排的驚喜惜別會,來參加的有好幾百人,許多是我的病人,有政要代表,也有華人朋友,許多人講了感性的好話和祝福的話,最後還排隊握手道別,互道珍重再見。這是我們永生難忘的一次聚會。
人生就像一列行走的火車,每到了一站自然有人上車、下車,我覺得在北美洲生活的這二十五年的列車時間上,無論在智慧上、在能力上、在做人做事上,都是我一生中最豐富的一段。當我背著沉重的行李下車時,我告訴車上的人說要回我的故鄉台灣做一點事情,而留在我們行李背後的,除了對他們的感激、想念之外,還有我們兩個尚在讀大學的兒子。我禱願上帝眷顧他們,我也祈禱願全能的上帝能照顧我病友及教會的朋友,華人朋友及台灣同鄉會的朋友!

 開刀後填寫手術紀錄單
開刀後填寫手術紀錄單
Source from 回台灣買靈魂–門諾醫院.黃勝雄醫師回憶錄 10/2016
Posted in 01/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