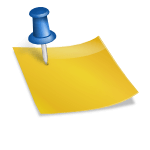我的自白
作者:謝昭梅(夏眉)
記得上小學時,我們學校有個圖書室;裡面只有一座書櫥,擺的是些童話故事書。那些兒童書大概值不了多少錢吧?可是對我們那個資源貧乏的國民學校來 說,卻很寳貝,都上了鎖。我常常在書櫥前面留連不去,卻從來沒有機會借到書。上了嘉義女中後,學校的圖書館書很多,可以隨便借回家看;我真是如魚得水,整 天沉浸於小說的世界裡,而把那些沉悶的教科書都擱在一邊了。我還喜歡到閲覽室去翻閲雜誌,看的無非是中文版的“讀者文摘”和當年很流行的“皇冠雜誌”。那 時的我,以為自己已跨進了“文學”的殿堂。
上初二那一年夏天,我姐姐從臺北回家渡假,她特地向同學借了一本書回來,要我看。原來那是一本翻譯小説,書名叫“猩紅文”,真是奇異古怪的名字!我 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才看完它。我只記得故事很吸引人,可是有許多曲折的情節我根本搞不清。畢竟,一個小孩子怎麼懂得那錯綜複雜的男女關係?怎麼可能瞭解作 者對於人性的描寫?
等上了大學,我才知道原來那本書的英文書名叫“A Scarlet Letter”, 是美國作家 Nathanial Hawthorne的名著。雖説我在中學時代根本沒看懂那本書,可是它卻啓發了我對外國文學的興。那時我們學校為了鼓勵學生養成閲讀的習慣,在教室裡擺放了不少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儒林外史”等,希望能引起我們的興趣。 我曾試過幾次,卻都中途而廢了;只覺那些書的筆調千篇一律,内容枯燥無味,每個角色都那麼窮酸迂腐, 讓人只想打瞌睡,實在提不起興致。後來我乾脆只看翻譯小說了。只覺那些外國小說,情節生動而有趣,一點都不乏味。
我在嘉義女中就這麼混了六年;有一天,我的級任老師不辭辛勞,坐了火車到我家去訪問。我母親藉這個機會詢問,“老師,聯考快到了,妳覺得我女兒有沒 有上榜的希望?”我那導師是教我們生物的,她躊躇了老半天才說,“恐怕不樂觀呢,她三天兩頭就閙胃痛,常常請病假,不上課。”我母親覺得很丟臉,事後她威 脅我說,“妳就不要升學了;乾脆去當店員吧?”
“媽,妳別信老師的話,我沒有她說的那麽差;我只是不屑上三民主義,也覺得生物課很無聊,所以常常偷跑出去看電影罷了。”
“妳有甚麼打算?想當店員吧?”
“我不知道呀;妳說呢?”
我雖然天生的任性與疏懶,但面臨緊要關頭,也懂得振作。結果,我考上了台大法律系。那份得意!整個夏天都像飄浮在雲端。母親也高興,她說,“唸法律系嚒?倒也蠻合適;妳平日喜歡跟我拌嘴,將來畢業以後,出來當律師,可以整天跟人擡槓。”
我是帶著怎樣崇高的志願,抱著怎樣無盡的野心走進大學校門的。可惜的是,好景不長,我上了一年法律系的課程,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根本不是讀書的料 子。什麼憲法啦,民法啦,我完全搞不懂。明明白紙上印了黑字,明明每一個字我都認得,可是把那些字堆疊在一起,成了一個句子,成了一段文章,我就不知所云 了。我不是沒試過,卻實在無法抓住文章的含意;那種失落與挫折感,至今回想,還心有餘悸。果然,年終期考完畢,我就知道災情慘重了,大概逃不過被留級的命 運。我每天在家窮緊張,像等待被判刑的囚犯。幸好成績單寄來以後,我一看,每一門跟法律有關的學科都險險地掛在六十分的邊緣,唯獨憲法一科沒逃過。我實在 很洩氣,也沒臉在家呆下去;於是匆匆地坐火車北上,躲回學校去了。我在宿舍裡一邊準備補考,一邊申請轉系。幸好校方很有仁心,一點也不刁難;結果我不但通 過補考,而且順利轉到外文系去;真是謝天謝地!
我怎麼去描述在外文系那三年的感受呢?可以說,如坐春風吧?讀書,成了一種樂趣。西洋文學史,英國十九世紀小説,美國散文,英詩,美國小説,希臘神 話,希臘悲喜劇,荷馬史詩 … 在我的心目中,每一個科目都是那麽吸引人,有的就像春風,像陽光,像新鮮空氣,像碧綠的海灘,使人嚮往,使人陶醉。有的像高山,等待你去攀登;有的像森 林,等你去探險,向你挑戰。如果說,研讀這些文學作品也算是做學問,那麼做學問可説是一種陶冶身心,增添生活情趣的追求;我一點都不在乎。況且有那些教授 熱心的指引,使我懂得如何做有系統的研究,如何挑出每一個作品的精髓;如何瞭解每一個作家的特點與筆調。我想,求知是一個人自身的需求,是精神上的提昇, 是一種至高的享受。
大學畢業以後,我不知天高地厚,野心勃勃地隻身到美國來繼續研讀英國文學。如今回望,不禁嘆息;當年的我,多麼天真!我憑什麼去跟美國人競逐?畢 竟,英語是他們的母語呀!他們一齣莎士比亞的戲劇,只需花一堂課的時間去分析研讀,就算完了事。哪像我在大學時,整個學期只讀了兩齣劇?那課堂的進程速 度,無異是龜與兔的差別了。單是莎士比亞還不打緊,最讓我頭痛的一堂課是“字源學”。這門學科,我在臺灣根本沒聼過,更甭提有任何的瞭解了;它的枯燥無 味,艱深難懂,使我畏怯。結果只讀了兩個月的研究所,我就逃之夭夭了。其實我逃離學校,不只是因為無法面對課堂裡的挑戰,更因為口袋的拮据,給了我雙重的 壓力。於是不告而別,逃到紐約去打工;心想,先賺點錢,隔年再轉校轉系,另起爐灶吧。
怎料,剛到紐約,就有不少孤魂野鬼似的單身漢上門來了。這些留學生長期住在紐約,都已經有了一把年紀(至少也在三十而立的年歲了吧?),都在物色對 象;偏偏當年女留學生奇少,實在沒得讓他們挑,如今聽説有個新面孔出現,於是都爭先恐後來報到,想看看廬山真面目!那一陣子,我可真風光!可惜,我這副長 相!沒多久,那些單身漢都被我嚇跑了;只有一個留下來。於是我來個急轉彎,把求學的野心與抱負都擱在一邊,而心甘情願地擔當起了妻子,母親,和家庭主婦的 責任。
可以說,結婚以後的日子過得很輕鬆,也沒有什麼煩惱。於是漸漸地,我又舊病復發了,一有空就抱着書看。那一陣子,我每隔幾天就帶著孩子到鎮上的圖書館去借書;借的無非是些暢銷書,言情小説等等; 書讀得很雜,沒有一點兒頭緒。屈指算算,才幾年的光陰?我已經把大學時代教授們的教誨與指導都抛到九霄雲外去了。我什麽書都看,都囫圇吞下去。我看的無非是毛姆(Maugham),約翰奧哈拉 (John O’Hara) 及Daphne du Maurier的小說,完全是為了消遣,為了打發時間而已。遺憾的是,我當時只顧自己看小説,卻從來就沒想到要借幾本兒童書,唸給孩子聽,藉此啓發他們的心智,鼓勵他們讀書的習慣。如今回想,不免汗顔。
等孩子進了中學,我才又回到研究所去修課;不過,我已學乖了,不再好高騖遠,不敢懷抱什麽野心大志;只選擇了實用的圖書館系。兩年以後,我順利地取得了碩士學位,也在附近一家大學的東亞圖書館找到了一份職位。從此,我開始了“讀書人”的生涯。
我爲什麼用如此美好的名稱來標榜自己呢?不為別的,只因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看書。我們的圖書館每年花幾十萬塊,買進了幾千冊的中文書;這些書包羅萬 象,有西洋的文學,歷史,哲學與地理,但大多是有關中國與日本的文明(包括歷史,地理,文學,哲學,考古,天文等等)。那堆滿了倉庫的書,都需要有人一一 過目,而且還要有系統地依内容去歸類;否則怎麼知道哪些書應該擺在哪個書架上?於是乎,我被派上了用場。我取過一本書來,先翻翻書面與書背,看清了書名及 作者,然後確定一下出版日期。接下來便開始猜測,到底手上這本書的内容是什麼?有的書一目了然,很容易就解決掉。有的書卻頗費心思,必須閲讀目錄及内容提 要。若是看了提要,還是搞不懂,就只好花點時間,認真地把書翻看一遍。可是,有時花了老半天的時間,仍舊毫無頭緒,這時只好求救於參考書了。偶爾踫到棘手 的,我把腦子裡的墨汁絞盡,仍舊一籌莫展。如此狼狽的境況,屢屢發生,實在很令人尷尬。終於,我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學識太淺薄。怎麽辦呢?唯一的解決辦法 是增進自己的知識。於是我首先在大學部修了三年日文,然後到研究所去選修明史,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元曲,金瓶梅,紅樓夢。這些學科都是我年輕時代不 肯去碰的老古董;如今爲了飯碗,只好埋頭苦幹了。可喜的是,我因此學會了如何欣賞“水滸傳”及“紅樓夢”。但是我的根底畢竟太淺,雖然修了幾年的課,依舊 是個半瓶醋,學識也不見長進;仍舊經常被手裡的書所考倒。有時花了幾個小時的時間,還是搞不懂,我不禁惱羞成怒,乾脆把書一丟,丟到桌子底下的一個大紙箱 裡,從此不再為了它而頭痛煩惱。也許有人會笑我,說我沒有職業道德?這一點,我也只好承認了。不過,我到底還是有點良心,每想及那些作者,不知花了多少的 心血才完成的著作,卻被我冷藏起來,我心裡不無愧怍。
我自稱是個讀書人,每天翻看十幾本書,卻都只看到皮毛,只摸到了書面與書背;這怎麼算是讀書呢?偶爾,我會碰到一本很喜歡看的書,真是不忍釋手;可 是我卻不敢貪婪,不敢留戀,只匆匆地過目就放置一邊了。二十五年下來,這麼囫圇吞棗的讀書方式,都已成習慣,我早已忘了怎麼好好兒地把一本書從頭到尾看完 了。而且在不知不覺間,我已把讀書看成了是一種累贅,一種心理負擔。俄國作家契柯夫 (Anton Chekhov ) 說,“告訴我你讀的是什麼書,我就可以知道你是一個怎樣的人。”到底我讀的是什麼書?我是一個怎樣的人?我自己都不知道。
原載於:臺灣公論報2009年5月8日
源自 謝昭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