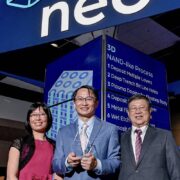廖清山筆下飄泊的台灣人(解說)
作者彭瑞金
旅居海外迄今已有二十餘年的廖淸山,從1980年才開始陸續在此地的報刊發表他的小說創作,收集在《年輪邊緣》裡的十二篇作品,便是他這些年來的成績單。
1980年,在台灣文學的發展史上,正是本土意識運動渡過驚濤駭浪,由一種狂緩而趨於止水的階段:易言之,運動的火焰止媳之後,似乎也使得夾在這個運動中吆喝的人群淸醒地認識到所謂鄕土文學者,本身仍是個極端空泛的文學體格。他們一時還無法從運動勝利的狂熱後,找到鄕土文學的標竿,這是令人十分迷惑的事情,有些人疑惑於何以論戰中 自己捨命據守的堡壘竟是如此脆弱空疏,因而運動後兩種典型的影響是:認識到文學的無力感,棄城而走另尋替代品,或埋首構築工事以潛心創作鞏固鄕土文學的堡壘。從遞變的角度看,1980年不愧是個台灣文學換血的年代,我們看到新人倍出的新景氣,也就是所謂從肯定鄕土文學的基礎出發的新世代,這群以本土意識做爲創作基點的文壇生力軍,雖然嚴重忽略了台灣文學中的本土意識並非創生於鄕土文學運動的事實,不過毫無疑問的,他們已經跨越輕薄鄙俗的鄕土感染熱,落實了台灣文學中的本土意識。認眞說來,他們一心一意想透過文學創作,關心、疼愛、護衞生養他們的土地,有心要扶持生存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找回自尊與莊嚴,使他們能帶着希望、信心走下去。因此發展出一種相當實用的文學觀念來,將文學融入台灣社會、文化改造運動中而成爲主力的一環,也許正因爲有這樣落實而執着的創作理念,因此被批評為缺乏巨視性的觀念與世界觀的照拂。不過,毫無疑問的,這是台灣文學的過渡時期,誰也不便逆料它將結出怎樣的果實來。
廖淸山正是屬於這個世代,衆多勤勉耕耘、埋首創作、具有強烈文學本土化意願的作家之一。歷經鄕土文學運動的洗禮之後,這個世代的新作家已經能夠無驚無懼、不躱不藏地闡釋他的本土情懷,儼然形成一股巨流。廖淸山長年旅居海外,在這股巨流中尤顯突出的是海外台灣人的經驗世界。 過去島內雖不缺乏以旅居海外人士爲背景的留學生文學,或得了便宜還賣乖的、以煊揚海外華人社會兼做鄕愁渲洩、被稱爲脫逃文學的非台灣文學:像廖淸山那樣,將作品的焦點定在台灣,與島內台灣文學同氣合流的,則是鳳毛麟角。收集在《年輪邊緣》中的十二篇作品,故事發展的空間雖然跨越台美兩地,但無可置疑的是以台灣爲焦點的創作。敍述旅居美國的台灣人一所謂台美族的艱難處境,以及從台美族人眼中照現的台灣社會病灶,應是這些作品的兩大主題。故 事的舞台雖不在台灣,卻絲毫無損於以台灣爲基準的思考方式,我以爲廖淸山的小說開闢了一條台灣小說嶄新的支流。
從這十二篇小說的故事內容分析,故事的主人翁不外是六〇年代以後旅美的台灣人,他們有的放棄原有的優異職位、工作機會,或者原本安定的生活,爲着某些表面看來十分虛幻而空洞的理由,來到新大陸,面臨一切從頭來過的新局面,開始他們艱辛的新旅程。作者在描述這些人物的時候,採取的是簡約方式,並不深究他們赴美的動機,也無意觀照整個台美族,僅凸顯了一撮受困於美國社會的台美族人,倉惶失據所受的凌辱,落魄、失意……顯然作者觀照這個族群時,所用的濾色鏡是台灣的。他並無意爲困局中的台美族人代言什麼,或抗爭什麼;相反的,他的小說主題似乎是從這群人身上的問號出發——他們何苦到這裡來受此難、受此苦?當然這之間作者並無責難的口氣,只是一種探索、思考,而頗有「孰令致之」的意味。這絕不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我們 姑且檢視這十二篇作品的主人翁,哪一個不是別有所圚、想盡辦法,甚至鑽弄營求、自願赴美的?我看不出來作者有任何嘲弄的筆調,卻似乎看到作者張着嘴問這群人何苦來哉的口勢。也許這「何苦來哉」正就是今天的台美族最不容易解釋的心結,而這正好是廖淸山小說的出發點。這些小說的創作企圖打開這群人的心結,何以抛棄原本舒適安定的生活離鄕背井,將自己投入這個充滿種族歧視、生存競爭激烈的陌生世界?雖然廖淸山的小說並未明白勾勒出這些台美族故事 的背景,特別是他們的心靈世界,不過一些弦外之音已經足以證明這些從台灣社會離心力甩落的異鄕漂泊者都藏着一個共同的故事——都是一個特別的時代、特殊意識下的產物,從這一點看,廖淸山的小說似乎提出了這樣的課題:爲什麼那麼多台灣人選擇了流浪和漂泊,寧願受苦?
廖淸山的小說崛起於意識掛帥的八〇年代台灣文學新洪流裡,以具有自然主義傾向的寫實手法,極富特色,我們在這之間看不到可以稱爲口號的東西,只是輕輕地一再提出相同的問號,但卻可隱約的感受到台美族內心「給我新環境」、「新世界」失望後的吶喊。因此這些以台美族爲中心的小說, 基本上依然刻寫的是「台灣」。當我們讀到〈荒冷帷幕〉這 篇頗具典型的作品,描寫一對來自屛東鄕下的小夫妻,丈夫當貿易公司業務員,太太是小學敎員,爲了掙脫命運的枷鎖,放棄還過得去的生活,置身舉目無親的新大陸,忍受「風吹雨打」,丈夫擔任倉庫管理員,待遇菲薄,工作時間又長, 太太上成人學校,來自白人的騷擾,黑族的歧視,與黑人、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雜處的屈辱,生活一如驚弓之鳥。「但頭已洗,不剃也不行」、「爲了爭一口氣,一定要留」,這個並未被特意誇飾的不如意的台美族的故事,實際上也就是這本小說集中台美族的典型。他們可能以不盡相同的理由赴美,卻無疑都是帶着對台灣的失望、和對新大陸的無限憧憬而來,他們企圖在美國這塊新天地找尋他們在台灣所沒有的,至於到底是些什麼,我也不知道,廖淸山是否居於小說藝術的理由故意不予道破,還是存心留給讀者去感覺?
總之,這些作品在若隱若現中照現了相當廣濶的台美族問題,例如〈荒冷帷幕〉中的小夫妻曾振榮與詹淑玲面臨居留問題,受到勞力剝削,倉皇不可終曰;〈執〉則試著從宗敎界人士的神與財貨、情愛的糾葛中理出神職人員的眉目來;〈誦經〉描寫在汽車旅館打工的留學生夫妻面對充满淫慾的噁心世界的無奈:〈老朋友〉寫道不同的兩種台灣人;〈消失〉寫因送貨遭黑人強姦生子的留學生夫妻導至的離異;〈年輪邊緣〉寫一個曾經受政治迫害而在祭壇上證道三十五年驀然驚覺的牧師:〈裸之定點〉寫台灣政治陰影下變形的愛情與婚姻;〈結局〉寫中、台惡意誤解造成的破裂婚姻;〈潮〉寫流落在美國不幸淪做肚皮出租的台灣婦女。這九篇小說大約就是廖淸山筆下台美族的群像了,也許我們的確無法用一條粗而明顯的意識繩索將這樣的台美族串接起來,不過,這些文學毫無疑問的是傳達了一群「老感到惶恐、戰慄、想哭,卻又哭不出來」的、不快樂的人群的心聲。値得注目的是,從故事的取材、作品世界的空間而言,這些廣泛的台美世界都明顯的以「台灣」做爲這些人物思念、痛苦、傷感、回憶的原點,他們的悲傷和痛苦有的是來自和過去的在台灣的生活的比較,有的是直接背負了「台灣人」的十字架,有的正在驗收台灣人血流中的原罪,有的是台灣政治的受害者……,不一而足,廖淸山似乎有意將他們變成一面鏡子,一方面照出台美族的生活與心靈,一方面切穿台灣人的心,所以我認爲這些是另一個形式的台灣文學。要之,他們所面對的災難與悲劇,諸多是和他們背負的「台灣人」命運有着極深的關係,奇怪的是,廖淸山的筆下沒有一個得意的台灣人,也沒有一件得意的台灣事。對於長年羈旅海外、心繫故園的台灣人作家而言,豈不又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另外的三篇小說:〈灰色的條件〉、〈隔絕〉、〈遺產〉則是直接寫到了台灣的人與事。〈隔絕〉寫的是安步當車的受薪階層的台美族與島內暴發戶的心靈距離;〈灰色的條件〉則暴露了另一種形態的島內暴發戶——民意代表——喪失天良、享盡特權……的酿惡姿態。〈遺產〉較特別,描述一件涉及島內外親友因遺產繼承事件而表現出的貪慾與無知。這三篇小說批判性最強,暴露最多,也唯有透過這三篇作品,我們才能較淸晰的看到廖淸山小說對台灣的關懷層面。
總體而言•廖淸山的小說始終保持相當冷靜的筆觸,許多「故事」可能還保留了相當程度的原貌;這和同時期許多加油加醋的台灣小說相形之下,淸新、眞實的特質很容易被感覺出來。不過可能也正因爲如此,這些作品斯文、儒雅的特質,顯然也將自己的創作侷限在純知識人的感與思上。在一個急切需求文學功利,文學充满濃重社會使命感的時代浪潮裎,也同時暴露了其薄弱、織細的一面。也許眼前這些作品對一個終身以之的作家而言,僅只是開始,任何綜合的評價都只是變相的期待。不過拘謹的知識人眼光,流水般自然的敍事筆法,廣博的作品世界,很可能使得這些具有漂泊者自覺的作品,不幸在廣大無際的意識之海漂泊;尤其是這些略顯著急地以台灣爲中心的小說,「台灣」卻在作品中面臨著被抽象、意念化的危險,畢竟這一切不過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充满無奈的台灣人的「遊子吟」。
摘自 年輪邊緣/1997/09 作者 廖清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