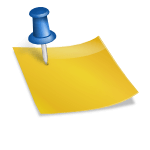我走過的語言路程
林壽英
台灣在日本統治時代,我父親從日本留學回台灣與母親結婚後,便回到屏東縣萬巒鄉下一個叫泗溝水的客家小農村之祖居老家,與年邁、守寡的阿婆(我的祖母)共同居住。1943年我出生於泗溝水這個客家小農村。 當時,全村的居民男女老幼都講四縣腔的客家語,因此,四縣腔的臺灣客家語是我的母語,我是台灣的客家人。受日本教育的父母親,在家時,日常生活中的交談都用客家話,只有三不五時父母親之間講一些不讓我們兄弟姊妹們聴懂之事時,他們會使用日本話。我的二伯母是二伯父去日本留學時,娶回臺灣的日本人,二伯父母及堂弟一家三口也住在泗溝水。二伯母常來我家看阿婆,二伯母雖然入鄉隨俗學了一些客家話,但她跟我父母親交談時,他們之間都用日本話。童年在耳濡目染的環境下,我雖然不會講日本話,但對日語聴得很熟悉,也懂一些日語。
當年,我父親任職於屏東、潮州鎮由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HO) 所屬的瘧疾研究所,我常有機會去該所參觀。WHO經常派一些講英語的西洋人學者來瘧疾研究所任職,他們有些是携眷 (妻子、女兒) 同來,因此,我上中學之前就曾有機會接觸過一些洋人,也聽到過英語。
我的叔父從日本學醫回台灣後,在潮州鎮開業行醫。童年時,阿婆有時會帶我一起去潮州的叔父家住幾天。那時候我注意到叔叔的附近鄰居們都不講客家話,而是講另一種我聽不懂的語言 (福佬話) ,我才知道除了客家話外,台灣還有福佬話,而且多數台灣人是講福佬話的。
1949年,我六歲進入萬巒國民小學一年級時,開始學漢文及北京話 (mandarin) 。北京話跟我的母語 (四縣腔的客家話) 似乎很接近,學起來就輕駕熟,不感到有何困難。學校規定在校上學時,必須講北京話 (所謂的國語) ,但放學後回到家裡及下課後跟同學們玩樂時,我們都講母語客家話。
1955年,我上屏東女中初中一年级時 (見圖) ,開始學英語文。初中一、二年級,我們的英文老師是一位年輕又活潑、時髦的黃蘇萊女老師。她是屏東空軍基地的一位空軍軍官夫人。聽說黃蘇萊老師住過美國,因此她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她有個外號,叫 [美援的] 。黃老師上課方式很活潑,注重發音、讀及簡單會話,很少講解文法,她的教學方式增加不少我學習英語文的興趣。屏女高中時,我們的英文老師是一位風趣幽默,從師範大學英語文系畢業的張福全老師。張老師不但英文教得頂呱呱,而且時常在課堂上開自己的玩笑,和學生們笑成一團,讓我們上英文課時充滿了歡樂的笑聲。我每次想到張老師時,都還想笑。哦! 差一點忘了告訴讀者們,學生們给張老師取的外號是 [红豆湯] ,他是一位令我難忘的老師之一 。
我泗溝水的家離屏東市內的屏東女中,路途遙遠,交通不便,無法通學,因此我在屏女的六年 (初、高中各三年) ,除了寒暑假外,都寄居在屏女的日本式建築之學生宿舍。那時候,寄宿生中有不少是從山地來的原住民學生,她們大都是排灣族或魯凱族,她們彼此之間講她們的母語時,我都聽不懂。讓當時的我又見識了台灣的另種地方語言! 屏女宿舍裡生活規律嚴緊,每天晚飯後,規定學生們必須坐在飯廳裡自修、作功課,直到十點就寢。不下雨時,管理宿舍的舍監允許我們晚自習中有半小時的休息時間,可以走到宿舍門前的大操場上,聊天、運動或嬉戲。這時,原住民的住宿生就一起用她們美妙嘹亮的歌聲開始以母語唱原住民歌曲,手牽手豪放地跳山地舞。非原住民的我們也時常加入她們的歌舞行列中同樂。晚間在皎潔的月光下,同學大家一起在青翠草地的操場上盡情歌舞的情景,令人終身難忘! 我至今都還記得、也還會唱那首當時常唱的排灣族歌舞曲。
屏女高中畢業後,1961年夏末,我去台中上中興大學。大一時可選修外國語文 (英文、日文或德文) ,因我父母親及很多長輩們都會說日語,我當年就選修了日文。我們的日文老師是一位中國東北出生,去日本留學,而後,來台灣的中國人。真失禮,我竟忘了這位老師的尊姓大名。老師的日語說得非常流利,他的外表、舉止行動,彬彬有禮,很像日本人。我學了一年的日語文,在學校生活都講北京話,課外時很少有用日語文的機會。大學畢業後,在台北的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 (NAMRU-2) 工作两年 (1965 – 1967) ,然後來了美國留學,幾十年來,我幾乎把日語都忘光了。直到我從支加哥北郊的 Abbott 藥廠退休,於2014年底搬來北加州東灣後,又開始在東灣的台灣人長樂會之日語班學日語。在郭敏俊日語老師的指導下,我們讀日文、唱日語歌,又演日語話劇,真是其樂無窮。很可惜,我們的日語班在2017年夏天就停止了。
1967年夏天,我到支加哥北郊的西北大學就讀,並和未婚夫 (現在的外子) 結婚。當年,西北大學有不少台灣來的台灣人留學生,台灣學生們有機會見面相聚時,大都用福佬話交談。當時,我聽不太懂,也完全不會講福佬話,為了要加入台灣學生的圈子,我開始很用心學講福佬話。西北大學畢業後,在支加哥北郊的 Abbott 就職期間,我熱衷參加支加哥台灣同鄉會及中西部台灣人夏令會的活動。那時候,我都能以輪轉的福佬話台語和台美鄉親們交談。
記得 1965年的夏天,我在台灣和現在的外子訂婚時,我去屏東、南州拜訪未來的公公婆婆 (外子的父母親 ) 。那時,我無法跟他們交談,因我完全不會講福佬話,而他們倆只會講福佬話。來美國十年後,1977年底,我帶两個兒女回台灣去探望公公婆婆時,他們都很驚訝聽到我說一囗輪轉的福佬話。他們問我,福佬話在那裏學的?我回答說:[在美國學的!] 。的的確確,我的福佬話台語是在美國跟台灣鄉親們學來的。
我一向對南美洲的風土人情有興趣,經過幾次南美洲之旅遊後,2003年底,我開始在當時住家 (支加哥北郊) 附近的 Community College 學西班牙語。凡學一種新的語言,一定要敢開口練習輿人對講,語言才會進步。於是,我有機會去墨西哥人開的食品店買東西時,或碰到作庭園工作的講西班牙語人時,我就試着開口用西班牙語跟他們作簡短的寒喧問候。西班牙語在美國是很通用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在家或參加台美人活動時,都講福佬話;跟我的兄弟姊妹及客家鄉親交談時,都用母語客家話;跟我的兒女及孫兒女、還有洋人或其他亞裔人,就講英語;早晨去公園和中國人一起打太極拳時,就只得講北京話。有機會學習及使用多種語言真是一大福氣! 讀者們,您同意嗎?

1955年作者(左)初一時與同窗好友在屏東女中校門口合照
Source from Mrs. Christine Yang/CA
Posted in 08/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