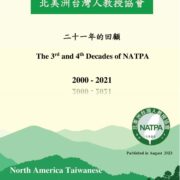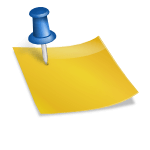我的學思歷程
李遠哲
我成長的時候是在變動的時代裡,剛上小學就因爲盟軍的轟炸而整整躲了兩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我看到整個世界的變遷,如台灣的光複、大陸的淪陷, 不過在我年輕的歲月裡,就讀台大前有一件事是我一生的轉捩點;我在高一時曾經病了一陣子,醫生說我一個月不能上學,倒在病床上休養,每天思考初中這三年過的生活,以及在書本上學到的事情,很多小說的描寫跟社會的變遷有關,也看到如甘地等偉人的傳記,不過高中以前常在床上想的是,小時候做過各種各樣瘋狂的事,喜歡打球就拼命的打乒乓、打棒球、打網球,也參加樂隊、參加壁報比賽,好像生命是無限的,喜歡做的事都能做,但是高一生的那場病使我深深的體會到,人的生命並不是無限的,若要過有意義的生活,就必須好好規劃。所以一個月的臥病在床,讓我大徹大悟,使我了解到應該好好珍惜生命,希望人生過得有意義,當然我所謂有意義的人生,除了要過得快樂以外,更要爲人群生計做 出貢獻。臥床上的那一個月,我想到我的將來,我很喜歡科學家,希望自己將來成爲科學家。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科學和民主風浪很大,心裡也想著以科學救國,希望國家富強康樂,這也許是我能做到的。所以經過高一的那場病以後,我下定決心,要把握自己的生命,而不讓學校的教育擺佈我的生命,更不讓它擺佈我的生活。所以我在一九五九年,被保送台灣大學的時候,確實是滿懷著理想,我並不想在成爲很有名的人或是很偉大的人,只希望能過理想的生活,成爲一個很好的科學家,服務人群報效社會。
談到被保送台大化工系,念化工系是有幾個原因的:我父親是一個藝術家,小時候想學畫,看到父親作畫自己也拿著一張紙在旁邊想要跟著畫。父親總是說不要 學他的行業,養不活一家人的;那時候台灣的生活很苦。你大槪也聽過另一位畫家廖繼春跟他的兒子說:”沒有任何一個男孩子將來可以作畫家過活。”他也跟他的女兒說:”將來不能嫁給畫家。”你大槪也聽過林懷民先生談到,他小時候想學跳舞,他父親說:「這是一個乞丐的行業,將來若是當了乞丐不要找我。」因爲那個時候生活太苦了,尤其是當老師,家裡面人口多的話,是不容易養活一家人的。所以父親希望我念醫學院,但是我沒有接受父親的意見,念化工系可以說是一種妥協,一方面學工程總比學理科好。另一方面小學六年級看過一本(蘇聯的五年計劃故事),書裡面描寫工程師的偉大,怎麼把蘇聯從落後的農業國家,變成很進步的工業國家。這本書給我印象深刻,因此我想到化工系算是一個很好的妥協。我到台大上課不到兩個月,一直惦記著想要成爲一個科學家,也看到 二號館三樓的化學系教授,每天晩上都在作硏究,燈火通明好像整個台大舊址化學 系的老師都在努力作硏究工作,所以我就決定轉系。轉系那天很有趣,我在外面打網球,忽然想到今天是禮拜六,如果在十二點以前我再不申請轉系的話,就沒有機會了。看看手錶只剩三十分鐘就拿著球拍滿頭大汗的跑到化學系辦公室找系主任說,”系主任,我想轉系。”他問我說:”你是哪一系的學生?”我說:”化工系。”他說:”化工系如果念不好,到化學系還是念不好的。”我說:”不不不,我不是念不好。”他問我說:,你化學考幾分?,我說:”這個學期應該是九十分。”他說:”不錯,我在教化學系跟化工系兩班,只有兩個學生考九十分。”他看著我問我叫什麼名字,然後翻開抽屜打開他的本子確定這個名字沒有錯。那時候我一頭亂髮,滿頭大汗還拿著球拍的確不像是一個會念書的人,他看著我就說:”如果這位考九十分的學生是你的話,大槪沒什麼問題吧!”那一天我上了一堂很好的課,就是以後如果要去見系主任,你最好洗過澡穿一件乾淨的衣服去找他。我那一年認識了很多朋友,寢室裡有中部來的、南部來的,見識到所謂人外有人天外 有天,大家滿懷著各種不同的理想,我認識一位化學系高我兩屆的學長,他叫張昭鼎,這件事很有趣,因爲他弟弟張隆鼎跟我分在同一間宿舍,我就是經由他認識張昭鼎,知道他是學化學的,我又想轉化學系於是就問了他很多問題,我告訴他我希望成爲一個很好的化學家,問他如果好好念書,是否真的能成爲一個很好的化學家?他竟然說不會的,不可能的,於是很失望的問他: “爲什麼呢?”他說:”你知道二十世紀開始以後,原子物理的發展使我們真正能把握到微小粒子的動,你如果要學化學是要學一些量子力學的;但是從量子力學瞭解微小東西的運動之外,也還必須瞭解微小的 粒子與宏觀現象的關係;但是,要瞭解光現象的話,你還是要學一些熱力學、統計力學這一方面的東西;如果你要作實驗的話,也要學一些電磁學,這些都是化學系不教的。你也要學一些電子,如果你要涉獵一些文獻的話,你還要通曉外文,這也都不是化學系在教的。所以即使你好好念,也不太可能成爲一個很好科學家。,我跟他說: “我確實想成爲一個很好的科學家。”他說:”好啊,你就好好的自己來一番努力。”
所以那一年暑假,我跟張昭鼎約定好不回家,拿一本熱力學的書兩個人輪流講,就這樣待在宿舍裡念書,他念得還好,原文書我則是邊看邊査字典,一個暑假念 下來也還滿有心得的,這本書聽說在美國是硏究生程度看的,還滿難的,可是我們一個暑假下來也念了大半本,我跟張昭鼎有時候碰到一些困難的問題,就請教化學系的老師,他們總說你們還年輕不必懂這些東西,後來才知道他們也不一定懂。張昭鼎曾說要學電磁學、電子學、外文等等,大二時我就下定決心一一的去作,白天到物理系聽電磁學,晚上念電子學,同時那一年的晩上跟物理系鄭伯昆助教(他後來升任教授,才剛退休不久);以及新竹中學學長鄭文魁、鄭江水,四個人一起輪講一本由蘇聯人寫的原子物理的書,因爲當時我很想瞭解一些微小粒子的運動。一九五八年蘇聯發射人造衛星,那一年我念三年級,已經修了二年德文,但我還是決心學俄文。所以大學四年我很認真的學,想作一個很好的科學家,希望以爲社會貢獻力量。
那時候很多教授的硏究是靠大四學生作的,當時硏究所才剛成立不久,硏究生不多,因此大四學生也要作硏究,所以我在尋找指導教授的時候,也是受到張昭鼎 同學的影響,他說很多人喜歡跟有名的教授作,但名教授年紀都很大了,他們的思想不會很新,年輕的講師可能會有很多新的構想,於是我就找了一位叫鄭華生的講師指導,他確實是很努力,他當時住在新竹,可是每天做實驗做到三更半夜,就在實驗室睡覺,常常一個禮拜都沒有回家。我們一起作實驗的時候,他說比基尼核彈試爆的灰塵中發現很多放射性同位素,其中兩種同位素鋇跟鍶的微小量的分析,還沒找到很快就能分離這兩種離子的方法,也許可以用電泳的方式分解成功。我覺得這個題目很有趣,於是合作了一陣子的硏究工作。那時候我的思想以及學識很有限,曾經看過化學家除了用水溶液實驗以外,有時候也把氨當作溶劑作硏究,就是非水溶液的化學。那時候我就想可能鋇跟鍶被水分子包圍著,如果用酒精,因爲酒精跟包圍的水分子作用不一樣,也許再用電泳會分解得很快。後來證明我做的實驗確實是成功的。可是這小小的成功卻給我很大的信心,硏究只要全力以赴就會有結果。大學四年,我除了作科學硏究以外,也看了很多書,有些在當時還是禁書,像作家屠格涅夫、杜斯妥也夫斯基、巴金、魯迅的書,當然除了這些禁書以外,我也看了羅曼羅蘭寫的約翰克里司朵夫等。此外,也看一些政治經濟學基礎教材,有些硬的有些軟的,有些是形而上學的書,有些是歷史哲學的,的確看了很多書,所以大學這四年,雖然不能說自己有多大的學問,但是追求真理、努力探討、硏究新東西的這種幹勁,確實是非常充沛的。
我念淸華大學的時候,當時的原子科學硏究所剛成立,我們是第四屆硏究生,分爲物理、化學跟核工三組。我跟另兩位同學在化學組,雖然我在化學組,但是我念了很多與近代物理、核子物理有關的物理課,因爲我也很喜歡物理,因此在淸華的這幾年也念了不少物理有關書籍。不過到了硏二的時候就要開始寫畢業論文,那時候整個淸大大槪只有一位博士,因爲沒有資深的老師,就從海外邀請了一些學人,譬如從美國邀請一位學者來幫助原子爐,從日本邀請一位學者來教核化學,所以我就選擇了跟這位日本學者作硏究。那時候我記得很淸楚的是,因爲二次大戰結束不久,反日的情緒很高,尤其是從大陸來的人,因爲日本在南京大屠殺作了許多殘忍的事情,所以反日的情緒很高。日本在台灣還沒有作得那麼壞,但是在大陸和韓國作得很壞,所以日本教授在做我們論文指導的時候,有很多人還是不太高興的。不過我們至少要讓這位日本教授知道的是,台灣的學生絕不比日本的學生差。所以我們很努力也有很好的表現,果然他來了一個月之後就到處說,台灣的學生比日本的好,而且好很多。我跟他作化學硏究工作的時候,選擇的題目是”北投石的硏究”,因爲北投石有很多放射性的同位素,北投石是不溶解在酸或鹼性的溶液,你如果要把它熔解的話,要在高溫的白金鋼鍋裡面,用碳酸鈉先把它高溫熔在一起之後,才能溶在鹽酸裡面,所以這位濱口教授就在實驗室裡教我們如何先把北投石硏成粉末,再放在白金鋼鍋內高溫度燒。但是我記得曾經在”定量與分析”這本書中看過,如果化合物裡面有鉛,在白金鋼鍋裡面是不行的,因爲鉛跟白金和在一起會變成合金,所以應該先把鉛析出來,才能做這個工作。所以我站在旁邊跟這位日本教授說:”教授你這麼做可能不對吧?應該先把鉛析出來,也就是先放在鹽酸裡煮一天,析出硫酸鉛後再作下一步實驗。”這位日本教授聽了很不高興,他老遠的從日本來指導這位學生,沒想到只上幾堂課, 在實驗室裡教我們怎麼作實驗,眼前的小伙子馬上就告訴他說這樣做不對。他就不吭氣的在那裡花了三四天的功夫把這個分析的功夫做完,說這個硫酸鉛是百分之十七。我看了一下這個白鋼鍋,這裡面有一圈的合金,而我知道他得到的結果是不對的。後來我自己作,是百分之二十一,他的百分之十七比我少了四個百分點,因爲被白金吃掉了,變成一個圈,而這個白金鍋也糟蹋掉了。後來我寫我的碩士論文的時候,他已經回到日本,我寄到日本請他過目我的論文。他看了之後覺得我作得不錯應該發表在雜誌上,他就直接寄到一個雜誌上社去發表。但是等他登出來之後,我才發現他把我的百分之二十一改成百分之十七,這令我覺得非常失望,到現在爲止還覺得自己第一篇發表在雜誌上的論文,它的數據不對,因爲我的指導教授作實驗的方法不對,經過提醒之後他也不承認他的錯誤,這確實是不好的。但是也讓我學到了一點:不管你將來成爲多有名教授,還是要虛心的學習。
其實我在台灣的歲月裡,在台大或是淸華作硏究工作,都是相當辛苦的,因爲我 們從蒸餾水開始自備,很多藥劑、設備都要自己自備,常常晩上做到很晩,是繼續作呢?還是算了?反正作不出來?甚至週末吃過飯之後,要選擇繼續作呢?還是去看電影?每次遇到這種時候我還是選擇繼續堅持下去,在這樣困難的環境裡奮鬥的確是有好處的。我在柏克萊加州大學就學的時候,一九六二年當時柏克萊大學學運鬧得最厲害的地方,他們主張言論自由並舉行很龐大的示威活動,當時我以一個外國學生的身分來看柏克萊的學生,爲了理想而奮鬥的精神的確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爲理想,爲了正義願意付出很大的代價來參加這些活動,當然對我這個科學家來講,最好的事情是離開台灣,來到這沒有親戚、朋友的地方,只有我跟未婚妻兩個人在柏克萊,突然發現所有的時間都可以拿來做硏究,這真是以前所沒有想像到的,以前在新竹、在台北總有一些朋友來找你聊天,或是有一些婚喪喜慶的場面要參加。但是到加州大學的這幾年,才覺得自己是真正屬於實驗室,而不屬於社會的人。並在實驗室真正看到懂科學的人,許多教授真的是對學問懷著非常大的熱忱。真的想走入未知的世界找些新的東西,所以我在柏克萊的那幾年的確是如魚得水一般,因爲從柏克萊到現在爲止,我相信一個人會一直堅持的東西,才是他真正要的東西,也才學得最快,所以他們堅信爲了硏究而 學。所以我在柏克萊爲了做硏究而到機械工廠去學車床,關於電子方面的技術學了不少。那一陣子我因爲剛從台灣到美國,所以對很多事情的看法還很不習慣,例如我第一次實驗需用化學試劑,爲了省十五塊美金,我花了一個週末的時間在實驗室用了繁複的手續把它做出來,禮拜一拿到教室教授看了覺得非常不可思議,我告訴他:”我在淸華當硏究生的時候,一個月拿的薪水就是這十五塊美金。所以一個週末我可以幫省十五塊美金,這不是很好嗎?”教授馬上就拍著我的肩膀跟我說:”我有很多錢,不要爲我省這十五塊錢。”
剛到美國的時候聽說化學界有四位很傑出年輕人,其中一位在柏克萊,於是我在找指導教授的時候,決定要找這位教授做硏究。可是他當時已經收了很多學生, 所以不鼓勵我跟他做,於是我找了另外一位Mahan教授做,他曾寫過大學普通化學課本,跟他一起做硏究確實是很不一樣,他給我一個題目之後,第一個月我還常常回到辦公室問他,”這個問題是這麼解決嗎?怎樣做比較好?”他老是說:”遠哲,如果我知道的話,早就解決了!我知道的話,爲什麼要讓你來做呢?你自己想想吧! “所以我頭一個月很不習慣,問他什麼他都說不知道,我總覺得這個教授什麼都不懂似的。這是我人生的第二次大徹大悟,第一次是在中學生了一場大病之後,第二次則是在跟了這位教授做了一個多月的實驗之後,我覺得人生沒有什麼是可依靠的,除了家裡的老婆以外,作學問完全是要靠自己解決。當然後來我也知道,當一個人做的硏究工作是到世界的最前線,即將由已知走入未知的世界時,他的確是不曉得。所以我後來也在想,你如果跟一位老師做硏究,你問了很多問題老師都說:”我怎麼曉得?”你要好好問淸楚自己,這個老師是太懶惰,所以什麼都不知道嗎?還是他的知識已經推到人類的最前線,他知道什麼事情是知道的,什麼事情是不知道的,而這些老師是好的老師。如果一個老師在剛開始 的時候就叫你明天做這個,後天做那個,下個禮拜做這個,好像把你當他的兩雙手來用似的,那他可能就不是很好的指搏教授。我跟他做了兩年多硏究,解決了一些問題,有些事情原先的構想並不對,我們找到了新的實驗方法,兩年過去了,有一天他問我:”遠哲,你博士修完之後,想做什麼?”我覺得跟他這兩年當中也沒學到什麼,博士論文只有七十多頁,都是一些靠自己摸索出來的東西,他只是簽個名就讓我拿到博士學位,於是想繼續留下來做一些樣一個儀器。他看了半天總是看不懂,因爲這個儀器很複雜。他們常常說這個儀器可能只有五千年歷史的中國人才能做得出來。很興奮的看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事情,在哈佛大學的這一年半時間裡面,我很努力的做硏究,在外面跟很多學生做了不同的硏究也設計了一些的儀器。到了一年半快結束的時候,Herschbach教授說我已經可以離開,開始獨當一面的做硏究工作,找一份教職,但是Herschbach教授不讓我走,他說:”你做得這麼好,不應該從助教授開始,你應該是從有永久職位的副教授開始。”所以他要我再留一年,再開始找永久的副教授一職,但是實驗室的其他人覺得這樣不對,我應該從助教授開始好好的做,這樣可能對自己比較好。Herschbach教授仍然沒有介紹教職給我,到了三月的某一天,我跟Mahan教授說;”Herschbach教授好像不喜歡我離開他,他也不介紹那個學校在找人。”Mahan教授說:”我聽說科羅拉多大學好像在找人,你如果有興趣的話,就去試試看。”所以我就去了,三月已經很晩,可是真的還有一個教職缺,並接受我的求職,在我幾乎要到該大學的時候,就接到芝加哥大學打來的電話,說他們也在找人問我是否有興趣。我到芝加哥大學看了之後,就決定到這所大學去在芝加哥大學的這兩年,因爲我過去幾年做的博士後硏究,都是一些有創見、有創新的東西,因此倒是有很大信心。
在做了兩年的硏究工作以後,第二年的夏天有個重要的學術會議,我被邀請演講,因爲我的實驗室做出很多別人想做卻做不出來的事,所以有人曾問我說:”遠哲,晩上你在街上走路,難道你不怕嗎?”我起初也不了解這是什麼意思,他說:”很多在同一個領域競爭的人,快要因此失去他們的職業了。很多人以爲做了好幾年已經可以升副教授,但是跟你的工作一比,可能他們升不到副教授就要離開學校了。所以你晩上出去走路還是小心一點的好。”他這麼一講,我才想到很多東西是相對的,不過那一年我在那個硏討會上有三次演講的機會,講了三種不一樣的東西,倒是非常轟動。所以那個會開完之後,很多教授就說很不公平,說李遠哲爲什麼還是助教授?學校就馬上把我升等爲副教授,再過一年多就能把我升爲正教授。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在美國的社會裡面,我從來不斤斤計較這些東西,反而是別人一直在說應該怎麼樣應該怎麼樣,不過我在芝加哥總覺得那裡氣候太冷,冬天常下大雪,出門要把車子從雪裡頭鏟出來,有時引擎還發不動,害得我跑著去上課,常摔得頭上很多污泥到課堂上課。這時剛好加州的柏克萊大學問我有無意願回去任教,我就答應了,於是又回至風光明媚的加州。
也許是那一陣子我要離開芝加哥大學的時候,有一位西北大學的教授曾經提到過在芝加哥大學有一位年輕的教授做得不錯,說他要回到柏克萊大學,有一位就問 西北大學爲什麼不請我去呢?其中有一位教授還說,他可能以後會得諾貝爾獎的。 其實我並不曉得這麼一回事,但因爲他這麼一句話,就有傳言傳回台灣,我母親聽到了這個消息說,她那個很愛打球很愛玩的小孩,有可能得到諾貝爾獎。我跟我母親說”不會的,不可能的,不會有這種事的。”所以我每次回來的時候她都問我說:”你爲什麼還沒有得諾貝爾獎? “我就說:”這種事情是別人講著玩的,你怎麼把它當真呢?”我記得一九八五年我回來的時候,還告訴我母親說:”要得諾貝爾獎是不太可能的,做硏究最大的樂趣在於發現新的東西,尤其是跟學生在一起做實驗,知道這是世界上沒有人能作,只有我們能做,那種感覺是很高興的。”但是沒想到第二年我竟然真的拿了諾貝爾獎,我母親還很不高興的跟我說:”我去年問你的時候,你還說不可能,爲什麼今年就拿到了呢?”我就說:”我怎麼曉得?我是真的不曉得。”其實那個時候也有很多人問我說是不是步步爲營,要成爲一個很有名的科學家,或拿諾貝爾獎呢?沒有這回事,我真的希望能成爲一 個很好的科學家,然後爲人群社會做一點事。當然我年輕的時候經過高一的大徹大悟,倒是一個很有理想的人,在高中的時候把這個個人英雄主義都洗得非常乾淨,大家合作努力攜手邁進,這些想法倒是很徹底的。到台大的時候除了希望能成爲一個很好的科學家之外,還希望能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好好努力改造我們的社會,這些想法到目前爲止還是非常深刻的。
Source from Taiwan Tribune #1850 8/31/2000
Posted in 09/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