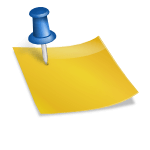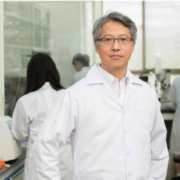活出淋漓盡致的生命(人生)
作者 林俊義
留學美國:從文學轉唸生物
坐完四十五天灰狗車以後,我就去印地安那州的哥森學院,決定一步也不出門,開始讀美國文學。讀一讀,有一些原因讓我想要換行。第一個原因是我有一個室友,讀心理的,有一次我跟他說:「我很喜歡你們美國的作家亨利梭羅,《湖濱散記》第二章:人生要簡單,生活也要簡單 」結果他回我一句:「誰是亨利梭羅?」這句話對我衝擊很大。我一個外國人來這裡讀你們的美國文學,講得嘴角冒泡,結果你連自己國家的大文學家都不知道!我失望之餘,開始懷疑要不要讀下去。當然現在回想起來,這種想法是不對的。
第二個原因是,我在台灣時,也有想讀科學的念頭。但我沒唸過高中,不知道讀科學要唸甲組,事實上我連甲組乙組是什麼也不知道。而且當時台灣的教育制度本身就是埋沒、壓抑一個人的潛能,現在大學有跨系讓你選修,以前考什麼系就修什麼課,我在外文系想讀科學也不可能;所以到美國之後,就想過將來可以來唸科學。
第三是現實上的考慮。我帶美金一千兩百元去,一學年的住和吃扣下來,只剩四百美元。文學把你帶到天堂去,現實又把你拖到地上來,所以想說讀科學也好。但是在大學時代,我數學、物理、化學都沒讀過,怎麼讀科學?後來想說一些社會評論者和作家,像寫《憤怒的葡萄》的史坦貝克、寫《推銷員之死》的亞瑟米勒,往往把社會當成一個生物體放在解剖台上觀察,用解剖的手法來描述社會現象,我感覺說這就是生物,生物和文學有關係,讀起來比較軟,所以就去生物系修生物學。雖然我的英文程度不錯,但上課還是聽不懂;還好我掌握一些讀書的訣竅,聽不懂就看教科書, 一本一本看,下了死工夫,一直讀一直讀,最後以全校第一名畢業。
在哥森期間,每個暑假我都跟一位美國教授做研究,我很認真學習,當他的助理,因為美國人不太想做研究助理。那教授也很奇怪,每天都沒做什麼,就從家裡到辦公室做研究,做到晚上才回去。我也整天跟他做研究(例如研究果蠅的黑色素、化學成因等),學了很多。他告訴我,他在印第安那大學唸生態學,如果我對生態學有興趣,就要到那所學校唸。當時印第安那大學生物系居全美五大之林,一些諾貝爾獎得主如發現DNA的華特生(James Dewey Watson)就是印第安那大學畢業的。他說你 要去讀,我考慮之後就去了,讀生物系研究所,那時是一九六七年。
服務非洲:體悟生命的奧秘
我就在研究所繼續深造,生態學一直讀一直讀,讀到一九七〇年時,有一種浮動不安的感覺,覺得這樣對嗎?生命難道只有讀書嗎?想去非洲。你在台灣如果說要去非洲,大家都說你是瘋子,台灣文化就是這樣子;但是我到現在為止,內心一直有個呼喚,我要再回去非洲。雖然我曾經去過非洲,但是想替非洲人做些事情的呼喚,始終都在我的心頭迴響。那次去非洲是一九七〇年,哥森學院和肯亞方面的教會合作,籌設肯亞專科學校生物系,校方詢問我的意願,我說好啊,就去了。去才知道,那是一個很偏僻、沒有電燈的地方,但是景色很美,可以看肯亞山。
我從一九七〇到一九七三年都在非洲。我的一個孩子在那裡出世,我在那裡得過瘧疾,也爬過非洲最高的吉力馬札羅山,什麼地方我都去過,所見所聞所感受的很多。我希望未來還有力氣時,能把在非洲對生命的探索、很多感動我的事情,用小說的形式寫出來。這次非洲之旅讓我覺得生命是一種非常神秘的、無法預測的東西。在台灣,讀書人往往什麼都不懂,只出一張嘴都不出手,所以電機博士連家裡的保險絲斷了,也不知道怎麼修;但是在非洲,蓋房子、修屋頂都要自己來,沒水的時候要想辦法牽水,有水了還要想辦法淨水,喝了不會拉肚子。啤酒不是沒有,就是熱滾滾的。我曾看見別的村莊餓死人,我也認識很多讓我感動的人,非洲人、外國人、傳教士都有。這些都是彌足珍貴的人生經驗,影響我很大。
透過非洲的經驗,讓我從只會出嘴不會出手的,到能夠全身趴在泥巴上面做事,慢慢了解實務經驗的重要性。一九七三年肯亞專科學校生物系成立了,招生結束後,我就離開非洲回到美國,那時就決定要回台灣。回想當初離台赴美,說莎拉吧永不回來,現在又想回來了,豈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但我想回台灣的意識非常強烈,因為非洲之旅給我很大的啟示,逼使我非回來為這塊土地做點事情不可。
一九七五年我回國了。當時台大和東海都要聘我,台大開出來的月薪是一萬二千元,東海只有七千四百元,但是我選擇東海。因為我回台北時,在那種政治環境下,知識份子都很苦悶,每天相約喝咖啡,時間都清談完了,做不了什麼事,所以我決定到東海做我自己的事情。
回台打拚:回饋故鄉不休息
在東海頭三年,我做研究、教學、出版很多論文,之後開始寫文章,關懷和批判環保政策、生態政策、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等。回想出國之前,十年一直在讀書;出國之後,從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五年,這十年也一直在讀書。我覺得我的人生很幸運,很少人有這種機會讀外文再來讀科學,而且擁有二十年的讀書機會,我覺得很感恩。所以回台灣以後,我就一直寫文章。從一九七五到現在二〇〇一年,二十五六年間,覺得每天都沒有休息的感覺;尤其在二十年前,每天不是演講,就是寫文章,晚上沒得睡,也是寫文章。那時還要教書,還要做研究,還要出版,一直工作,壓力很大,這個經驗也是很好,我覺得應該對台灣多付出一些,盡我所知多提一些建言。到現在為止,我雖然出版七、八本書,但是回頭看過去寫的,還有很多沒出版。
回顧這段人生,從一九六五到二〇〇〇年總共卅五年的歲月,我在探索人生和知識的過程中有一些心得,在此和大家分享。我深深覺得,生命這種東西是一種open system,開放體系。很多人用很多禁忌侷限生命,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限制潛 能的發揮,是很可惜的做法。從生態學來看,生態體系本來就是開放的,你要和外面 接觸;接觸以後,生命會導致什麼樣的變化和結果?Everything is possible。重點是你 要自己去做。
生態學給我的另一個啟示是多樣性,生命要做多樣性的發揮。我在東海任教時, 有一段時間覺得如果我一輩子當教授會很遺憾。我希望可以做很多不同的行業,像史懷哲也能修理車子,也能蓋房子,也能當音樂家,也能行醫,也能傳教,又是哲學家,又是校長等。生命本來就是這樣子,它是多麼珍貴的東西,一定要把它發揮得淋 漓盡致。
生態學教我多樣性是好的,所以我把這個理念應用到生活上每一個細節,對食物我都吃多樣性,一星期換來換去,不管什麼都吃。在生態學上,多樣性是生態體系穩定健康的基礎,也可應用到你的生命和生活中,你應用下去,絕對不會錯。已故的張光直教授是讓人欽佩的考古學家,我有一年在哈佛大學做研究,常常和他見面,他每次都說:「林教授,來吃飯!」都帶我去哈佛大學教授倶樂部裡面吃。我看他每天都挑一樣的吃,猜想他的身體會有潛在的危機;真的過了不久,他的身體就不太好了。
我們人都怕改變,怕去做不同的事情。但是生態學教我多樣性,演化學教我人絕對要改變。生命的過程是ever changing ,一直在變的,會發生什麼後果,你沒辦法預測。但我們不要把改變當成威脅,要把它當作機會,勇於接受挑戰,生命才能發揮得淋漓盡致。科學哲學教我們要做一個懷疑者,但不要做一個憤世嫉俗者,這是兩種不一樣的人。懷疑者會採取行動,尋求改變;憤世嫉俗者不知道人會變,也無法改變什麼,一支嘴每天只會抱怨。我這輩子最痛苦的,就是和一些台灣的教授聊政治,我說怎樣來做,他說沒有用啦,不會變的,一直講沒有用的理由。我就問他,為何不去想有用的一面,光講沒有用的一面?台灣文化、中國文化製造了 一大堆cynics (犬儒),只會說風涼話,不會採取行動。殊不知生命本身要發揮它的力量,一定要採取 很多行動;你不行動,什麼都不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