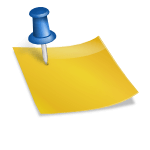當美國住院醫師的第一天
葉思雅
前言
從1960年代到1970年代前半,有很多台灣醫學院畢業生來美受intern(實習醫師)和resident(住院醫師)訓練,因爲當時美國醫學院畢業生本來就不多,加上有些畢業生被徵兵參加越戰,供不應求美國醫院的需要。這現象對台灣畢業生來說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很多人受訓完後,在美國醫院可找到開業的機會。當時有些醫院爲了幫助剛來美國的醫學生瞭解美國醫療系統的要點,給他們一些orientation資料,或給他們「新生訓練課」,讓他們熟悉美國醫療系統後才擔當臨床重要的任務。
我於1967年來美國進修醫學的途徑不同,台大醫院婦產科住院醫師訓練完成後,來美國耶魯大學醫學院當研究生,研究胎心音監護,沒有受一般臨床訓練。繼續研究工作幾年後,才發現要得到美國行醫執照與專家資格一定要經過一段美國醫院住院醫師訓練。我很幸運,於1974年有機會進入賓州大學醫院婦產科受訓,主任 Mastroianni 教授讓我只做二年的訓練(當時美國要求是四年:一年intern 與三年resident),我進去就當第一年 resident,二年後完成第三年resident。
以下就是1974年當第一年resident第一天的經過。
7月1日上午
我的第一個rotation 就是當private主治醫師的助手,與第二年住院醫師 Dr. B 同一組,照顧所有住院 private 病人(總共約20人)。Dr. B 叫我在早上五點半報到,與他一起巡看病人,因爲第一刀是 7點半開始,我們一定要7點整到達手術房準備一切,讓主治醫師在7點半動手。Dr. B與我就分手去看private病人。我因爲怕去手術房遲到,所以很認真、很快的看完病人,6點半就到達 Ravdin 大樓,當時手術房在第六樓。我很快的找到Ravdin 大樓的電梯,一進去就按六,可是電梯在六樓不停,繼續往上,下來時我再按六,電梯也不停繼續往下。我開始著急,以爲電梯懷了,連續試了二、三次,還是不停,心裡越急腦子也變得胡塗失去思考能力;後來決定在七樓走出電梯,從樓梯走下一樓。到達開刀房時,大家睜眼看我,以爲我不來了。在困窘情況下,腦子一清,恍然大悟,一般電梯本來就在手術房那樓不停,爲了避免感染。
一個早上幫助主治醫師開幾刀,心理漸漸安定下來,因爲是頭一天,我只有拉鈎子旁觀。有的醫師技術好,不到一個鐘頭就完成了子宮切除手術,有位主治醫師 Dr. H他一邊做D&C一邊哼歌曲,好像淘醉在不同的境界似的,忽然間歌聲停了,命令大家手術停止。後來一位護士小聲對我說他把病人的子宮壁穿破了,我欽佩 Dr. H. 面不改色,結果病人沒有副作用,二天後回家了。
7月1日下午
當所有private 病人全部開完刀後,已經近二點鐘了。因爲肚子餓,趕緊離開手術房往餐廳跑,可是只跑了三步,我的 beeper 在呼喚我了,顧不得餓肚,馬上打電話到病房,才知道有一位病人點滴塞住,須要重新打靜脈。我到了病房後,護士小姐給我一套新的靜脈打針接點滴的用具,我看了頭就痛了,因爲我從來沒有看過這種用具,與我過去在台大醫院用的完全不同。當我在研究注射針與導管構造時,病人問我說「你是不是新來的?」我很緊張的回答說「是,今天是我的第一天。」當時我閉着眼精不敢看她,好像在等待天塌下來似的;幾秒鐘後病人對我微笑的說「不要緊張,每個人都有第一次。我來教你如何用這種「蝴蝶式靜脈針」,我是麻醉科醫生,常常用這蝴蝶式靜脈針。接着她一步一步教我如何做,加上如何用繃帶固定點滴系統等。我學了這一套之後,對我以後的臨床工作很有用,也是我第一天當住院醫師最大的收獲,對這位麻醉科醫師感恩不盡。
正在忙着收拾靜脈點滴用具時,beeper 又響了,我趕緊打電話到病房,接電話的護士小姐很著急的說「葉醫師,請趕快來病房pronounce dead!」當時我不知道她要我做什麼,就趕上樓到病房,那位護士跑過來說「Dr. M 的病人是癌病末期,我想她已死了。」當時我連想都不想對她說「人已死了,妳應該通知她的主治醫師,妳爲什麼通知我?」她用不耐煩的眼光看我說「你一定是新來的,美國法律規定人死去時,一定要有醫師執照的人確定、宣佈死亡後,我們才可聯絡morgue(太平間)來把病人帶走。」我聽了感到很慚愧,趕快拿起聽筒確定病人心跳停止,用手電燈筒看病人已擴大、沒有反應的瞳孔,才簽名 pronounce dead。
7月1日晚上 到 7月2日早上
我開始住院醫師第一天就被排值夜班。賓州大學醫院婦產科當時每晚有四位住院醫師值班,因爲醫院病人多,一年生產約四千嬰兒。第三年住院醫師不須住在醫院,有急診或開刀時才進來,全婦產科住院病人都由第二年住院醫師負責,第一年住院醫師與intern負責產房全部的工作。值班開始時 intern 和我被值班的第二年住院醫師叫去開場訓話,他(Dr. F)是個很自傲的年輕醫師,他給我們訓話一頓之後,說他晚上睡眠很深,如果要叫他,我們一定要確定他起床雙腳站直立才算是清醒,否則他不能負責他所說的,當時intern和我都知道這一晚難度。我們就開始進產房工作。賓州大學醫院果然真忙,生產數量多,我們倆整個晚上都沒有睡覺的機會。因爲醫院位於費城黑人區,所以病人大部分是黑人。開始時很不容易聽懂他們的英文口音,可是不久就習慣了。記得那晚半夜三點左右護士來找我,說第七床孕婦的胎心監護器測到胎心跳降低到每分鐘60左右,當時我立刻知道情況不好,臍帶被壓住,應該立刻生出來才可避免胎兒頭腦受傷害;因爲我來美國是專門研究胎心監護的。我檢查她的時侯,發現子宮口已全開,我們立刻把她送進產房準備生產。再檢查時,胎兒頭部已下來幾公分,我問護士第二年住院醫師是否可聯絡到,她說他已經熟睡了,不容易吵醒他;我叫護士給我 forceps,不到一分鐘就把嬰兒拉出來了,嬰兒一下子就大哭,我們醫護人員都很高興。第二天早上我向Dr. F報告,他非常生氣,教訓我一頓,可是我對他說他在睡覺,很不容易吵醒他,爲了爭取時間,我只好把過去在台大醫院學到forceps的技術用上了,結果救了嬰兒,有什麼不對?
此後產房逐漸靜下來,當我想上床休息時,陽光已經從窗戶照進來了,我要振作精神再工作十小時才能回家休息。
當時我回想這24小時的經過,使我很擔心,因爲這只是一天而已,前面還有730天的住院醫師訓練生涯,我如何能渡過這種日子?可是後來再想起這一天,領悟到這種經驗就是訓練自己最好的機會。身爲外國人來到美國第一流醫院受訓,在二年中要完成別人四年的訓練,我一定要加倍努力,適應美國醫院制度,努力學習美國臨床醫學的要點,將來才能在美國社會迎頭趕上;如果我有不知道的事,應該虛心詢問,有時在病人面前坦白承認,我才有進一步學習的機會。現在回想起來,這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可是我始終都在感謝這第一天的經驗,它給我帶來以後豐富的美國臨床醫學生涯。
Source from 葉思雅
Posted in 10/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