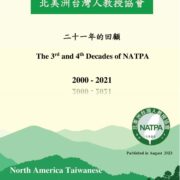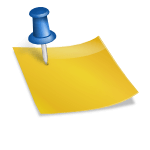和郭倍宏「不期而遇」
作者 葉治平
民報專文「郭倍宏會把民視帶向何方」 提到1989年郭倍宏以台獨聯盟主席的「一級要犯」身份, 潛返回台,現身中和運動場為「新國家聯線」造勢的精彩往事, 這又勾起了我參加那場歷史盛會的一些回憶。以我之見, 那場歷史性的造勢晚是台獨運動史上少有的精彩演出,值得記憶。 但這事件的始末,除了林文義在1991年出了一本薄薄的「 菅芒離土」之外,少有人提起。 我對郭倍宏進出台灣的策劃與細節一無所知,僅能就自己的記憶, 寫下幾次和他戲劇性的「不期而遇」, 以及參加那場造勢晚會前後的感想,希望留下一點見證, 同時也向那些敢在過去那段黑暗時期公開衝撞體制, 向外來政權挑戰的男女豪傑,表達最高的敬意。
和郭倍宏「不期而遇」
1989年鄭南榕為言論自由而自焚,我辭去工作, 和太太帶著五歲和三歲的兒女回到台灣。 雖然主要目的是為葉菊蘭助選,但在那風起雲湧的時代裡,我這「 無業遊民」所能參與的事務其實更多。除了葉菊蘭競選總部之外, 顏錦福那邊也來要人,環保聯盟和勞支會(後來的勞工陣線) 的抗爭都須要支援。更重要的是,好友陳婉真正轟轟烈烈的進行「 黑名單翻牆回家」的抗爭,這更是我必須參與的重點。
<第一次不期而遇>
因為我的時間較有彈性,所以任何抗爭總被「徵召」,而我也「 隨傳隨到」。那天,我接到通知, 婉真將到台北市選委會要求登記參選。因為國民黨不讓她恢復戶籍, 無法登記,所以抗爭行動一定會發生。我趕到現場時, 她已先帶幾個「衝組」上樓。 或許是在美國看過太多特務學生的惡行惡狀, 所以我到任何地方都先觀察四周,看看有沒有抓耙子混在群眾之中。 果然,在走進大樓時我注意到, 騎樓的公共電話旁站了一個不太像抗爭群眾的男子, 穿著一件紅色高領線衫,留著長髮,戴著墨鏡,一下假裝打電話, 一下又假裝看報,遮住臉部。我立刻警覺,這傢伙「似非善類」。 所以一面上樓,一面記著他的長像,準備要警告婉真, 等下可能會有狀況。但記憶忽然閃過腦門,我突然驚覺,那個「 可疑人物」不就是老友郭倍宏嗎!我一時沒有認出他, 因為在那時候, 全世界最不可能出現在台北街頭的人就是身為台獨聯盟主席「 一級要犯」的他。「這怎麼可能!但的確就是他!」 我心中非常激動,所以看到陳婉真立刻大喊,「我剛才看到倍宏!」 但她卻板著一張臭臉沒有理我。我想可能是抗爭進行中, 不便談這些事。
事後,婉真對我有點責難,「這種事情怎麼可以在那裡大聲小叫, 難道不知道四周都是抓耙子嗎?」原來, 她早就知道倍宏潛返回台的事,而且已經見和他過面,談了一些事。 我知道自己實在是警覺性不夠,感到有點尷尬, 但還是忍不住心中的興奮與感動。在那時,解嚴才剛兩年, 刑法100條仍在實施,社會上到處風聲鶴唳, 鎮暴警察的棍子棒棒見血。倍宏若是被捕,十年牢獄大概跑不掉。 他抱著犧牲的決心偷渡回台,想必也是受了鄭南榕的感召吧。
「台獨要犯潛返台灣」的風聲逐漸傳開,不久就在報上看到了「 據報,台獨聯盟主席郭倍宏偷渡回台,情治單位查證中」的報導。 過了幾天,又在聯合報上看到一篇更大幅的報導:「情治單位證實, 郭倍宏於昨日在台東偷渡上岸,警方已掌握行蹤,全面緝捕」。 我看了不禁哈哈大笑,倍宏早已在台灣到處趴趴走好幾天了, 國民黨的情治單位竟還煞有其事的「證實」,他是在「昨天」 偷渡上岸,這真的是太遜了。當然,國民黨也不是省油的燈。 所以我也請婉真轉告倍宏,他的模樣在人群中太過突出, 應該改變一下穿著與外表。
<在警察局不期而遇>
說倍宏「到處趴趴走」並不誇張。因為,過了幾天我又再次和他「 不期而遇」,而這次讓我更加吃驚。那天,陳婉真到內政部前抗爭, 要求恢復她的戶籍。她說沒有戶籍,無家可歸, 所以要在內政部前的廣場搭帳篷為家。當然,她的「家」 兩三下就被鎮暴警察踩平,她也遭到逮補, 送到古亭分局。我和幾個人隨即跟到,衝進警察局內靜坐抗議, 要求立刻釋放陳婉真。我坐在地上,正低頭思索下一步該怎麼做。 坐在旁邊的男子突然遞過一支煙,對我說「抽煙嗎」。我不抽煙, 所以只轉頭向他說聲謝謝。但張眼一看,卻讓我大吃一驚。 原來坐在我旁邊的,正就是郭倍宏。這怎麼可能! 國民黨情治單位在全台佈下天羅地網,重金懸賞,警騎四出, 全面追緝。而他卻悠哉悠哉的坐在警察局裡,要請我抽煙, 旁邊嚴陣以待的警察竟然渾然不知,這真的是太勁爆了。
我事先沒有注意到倍宏,因為警察局絕對是他最不可能出現的地方。 雖說「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但他的冷靜與膽大也真讓我佩服。此外,他也改變了造形。 剃了平頭,穿汗衫和球鞋,不抽煙的他也帶了一包煙; 不知有沒有嚼檳榔, 但看起來已七分像是龍山寺的那群「衝組」了。 我強壓住緊張激動的心,對他說:「多謝,那我們到外面去抽吧」。 我的目的除了要找個方便說話的地方,更是想趕快把他帶離警察局。
走到警局外面,我激動的和他握手,心中有千百個問題要問他,「 怎麼回來的?何時回來的?回來要做什麼?跑了那些地方?」 但我知道,這些問題都太過敏感,此時不宜問他。所以只是勸他, 現在風聲很緊,還是趕快偷渡出去,但他笑而不答。我也向他建議, 離台之前,可以到總統府或其他重要景點前照幾張「到此一遊」 的相片,等返美後再送到報社發表,一定會讓獨派士氣大振, 這樣就達到目的了。後來他的確拍了幾張照片, 包括站在警察旁邊那張。他也告訴我,因為上次被我認出, 所以決定要改變外形。他很得意的說,後來參加好幾個活動, 有看到我,但都沒被我認出來,顯然造形成功。我笑著說, 他真的很像「衝組」的模樣了,但風聲越來越緊, 還是趕快設法離開。
風聲的確是很緊。因為連我這種名不見經傳的人物, 只因每天和陳婉真接觸,都已遭到跟監。 自從郭倍宏潛返回台的消息傳出後, 每天早晚我家樓下就站了兩名剃小平頭的人物。 他們也大辣辣的露出對講機,讓我知道他們就是情治人員。 我和朋友開車南下去支援奇美化工的抗爭, 在台南市區竟被四名憲兵攔下,拿著自動步槍將我們押在路旁, 進行搜車。從美國返台到勞支會工作的一位好友, 因是婉真在洛杉磯的舊識,同時也支援她的抗爭, 竟有十多位情治人員在三更半夜衝進他家,說要搜補郭倍宏, 讓他的老母嚇得差點要送醫。現在再回想這些事, 感覺真是匪夷所思。 但對這些事的憤怒都被後來在中和運動場那場造勢晚會的激情與感動 沖得煙消雲散。尤其在散會後,竟在人潮中又和倍宏「不期而遇」, 現在回想起來更宛如做夢一般。
<造勢晚會>
那場歷史性的造勢晚會是由周慧瑛競選總幹事簡錫偕( 當時的勞支會會長)所策劃。 他事前先公開宣佈郭倍宏將現身造勢晚會,為「新國家連線」助陣, 引來近十萬群眾擁進現場,使得國民黨的鎮暴部隊難以出手。 他支援陳婉真的抗爭也是用類似的方法, 在抗爭現場附近的馬路及牆壁,以紅色噴漆噴上「陳婉真絕食抗議」 的大字,引來群眾前往現場圍觀,讓兇狠的鎮暴警察較為收斂。 對於他的足智多謀與臨危不亂,我非常佩服。
造勢晚會那天,婉真通知我早一點到顏錦福競選總部和她會合。 她說前晚和簡錫堦開會,有交辦一些事。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因為國民黨將會部署重兵,嚴陣以待,倍宏一旦現身, 想必是插翅難飛。想到這位曾在美國一起做學生運動的朋友, 被捕將面臨重刑,心裡十分難過。但到了總部, 看到婉真卻是一派輕鬆。她請顏錦福的保鏢兼司機 (綽號「老鼠」) 載我們到會場,因為時間還早,她建議先到「永和豆漿店」 吃些東西。我聽過這家店的名聲,但從沒有去過。今天來了, 卻完全食之無味。我看他們吃的津津有味,便問婉真, 簡錫堦交辦了什麼事?她輕鬆的回答,等一下我們要去接一個人, 負責送他到會場。我一聽,手中的燒餅差點掉到地上。莫非, 我們是負責去接倍宏!我又問,到那裡去接?她說在六點半左右, 中山路某地附近有一部黑色汽車停在路旁,閃著方向登, 我們過去就有人會過來接頭。這是那門子的指示? 但我的腦中卻只在想像,當我們一接觸, 埋伏四周的情治人員一湧而上,把我們逮捕的情景。
我們依約前往,我的心裡忐忑不安,不時張望四周, 回頭看看後面的車子。或許是心理作用, 所以每一輛看起來都像是特務跟監的車子。到了約定的地點, 天色已暗,因是下班時間,所以車子很多。 但我立刻注意到一個奇怪的現象, 因為停在路旁的車子每隔幾輛就有一輛是閃著方向燈的黑色轎車, 情形十分詭異。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們來來回回繞了幾次, 也不知道到底是那輛才是我們要接人的車子, 所以以不敢冒然停車去接觸。最後婉真對「老鼠」說, 時間差不多了,我們就別找了,直接到會場吧。我心想, 這怎麼可以,不是說要負責把人帶到會場嗎?但也沒多說什麼, 因為我已經學會,這類的事情,沒有必要知道,就不要多問。
事後我再回想這些經過,並和婉真談起, 才覺得自己真的是過份天真。 陳婉真是國民黨要抓郭倍宏所鎖定的關鍵人物, 早就被情治單位24小時監控,電話更被全面監聽, 若由她去接倍宏豈不是自投羅網。所以這些所謂「接人」, 開著車子在那裡繞來繞去,都只是誘敵之計,分散國民黨的注意力。 這也難怪,婉真能夠那麼鎮靜。不過我們研判, 停在路旁閃著方向燈的黑色轎車,可能都是警方的車子, 若過去接頭,可能就會被捕。這只是一個小插曲,但由此可知, 那天國民黨的確是佈下了天羅地網,誓將郭倍宏逮捕歸案。
到了會場,我們為了找停車的地方,先開到一間國小附近, 看到操場上已集結了好幾輛鎮暴車和大批的鎮暴警察在那裡待命, 所以趕快駛離。又開到一個工地,更讓我們大吃一驚, 因為裡面竟也躲著密密麻麻的鎮暴警察。 據說那天國民黨派出了近萬名的警力,所以附近只要有空地的場所, 可能都進駐了鎮暴警察,團團圍中和運動場。我在想, 以這樣的警力佈署,郭倍宏有可能突破重圍嗎?不可思議的是, 他真的做到了,而且是輕輕鬆鬆的走出會場,消失在人群之中!
那晚下著不算小的細雨,但中和運動場內外仍擠得水洩不通。 當晚來的助講員很多,除了盧修一,陳菊,尤清, 江蓋世等政治人物之外, 還有高俊明牧師和北美洲教授協會的廖述宗與陳文彥兩位教授, 全台各媒體的記者更是傾巢而出。在那沒有電視政論節目, 黨外雜誌繼續被查禁的年代裡,到造勢晚會聽演講是一大盛事, 聽眾總是欲罷而不能。但那晚大家卻都有些焦躁, 因為都在等待郭倍宏的出現的那一刻。時間越來越晚,雨越下越大, 現場的氣氛也越趨詭譎。場內群眾的情緒高張, 場外的鎮暴警察如臨大敵,蠢蠢欲動。而我的心中則是充滿著悲情, 為什麼台灣人想喊出一句台灣獨立,要受到如此的打壓與折磨。
歷史的時刻終於到來,陳菊唱完「黃昏的故鄉」後, 以她一貫沙啞磁性的聲調緩緩說道:「黃昏的故鄉, 故鄉在叫著倍宏,倍宏,你有聽到嗎?」全場靜默下來, 那是感傷與感性的時刻。她忽然一揚聲調說:「現在讓我們來歡迎, 咱的兄弟,郭!倍!宏!」全場歡聲雷動, 倍宏在幾個壯漢的簇擁下出現在台前。他穿著一件米黃色夾克, 帶著一幅黑框眼靜,還是理著小平頭。他神情平和, 面帶微笑的向群眾揮手致意,讓全台灣人看到, 這位被國民黨妖魔化,以重金懸賞的「台獨首惡」, 其實是就是這樣一位文質彬彬的台灣青年。
全場群眾情緒沸騰,跟著陳菊不斷高呼「郭倍宏!郭倍宏!」 甚至有人高喊「郭倍宏萬歲!」。一向最討厭喊萬歲的我, 也情不自禁的跟著高喊。我的熱淚盈眶, 看到四周的人竟也都是如此。在那一刻,我已經知道, 國民黨的鎮暴部對絕對不敢輕舉妄動, 因為全場的人都準備以生命來保護郭倍宏。警方若要強行上台逮補, 暴動一定會發生。這真的是偉大的時刻, 幾十年來被中國黨欺壓的鳥氣,隨著嘶聲吶的歡呼一吐而盡。 但在倍宏演講時,我又開始擔心:接下去會發生什麼? 鎮暴警察是否已經堵在會場門口?倍宏將如何走出會場?
但支持台灣獨立的群眾就是這麼可敬,他們讓不可能的事發生了。 郭倍宏的演講結束,造勢晚會接近尾聲,關鑑的時刻也已到來。 簡錫堦上台說,倍宏可能就要被捕, 請在場所有的人一起來見證這個歷史的一刻。 但就在高俊明牧師帶領所有人為倍宏祈禱時,台上的燈光突然媳滅。 緊接下來,像是電影情節一般,不可思意的事情就在我的眼前發生。 會場的燈光一盞接一盞熄滅, 連販賣香腸小吃的攤販也主動熄掉攤上的燈。在濛濛細雨下, 全場一片漆黑, 所有群眾帶上了在造勢會開始時主辦單位發給大家的「黑名單」 面具,開始在會場中跑來跑去。許多人一面奔跑,一面喊著「 我是郭倍宏,快來捉我」。大家難免撞來撞去,但沒有衝突, 只有歡呼與笑聲。整個場面看來是一團混亂, 但卻有一股無形的秩序,掌握著現場的變化。這個秩序就是, 大家同心協力,製造混亂來掩護郭倍宏安全離開, 而他真的也就安然的走出會場。
<人潮中又不期而遇>
這不但是驚奇,震奮,更是無懈可擊的精彩演出。 我高興得手足舞蹈,也不顧婉真還在台上, 跟著大家在會場中跑來跑去。 多年來台灣人飽受國民黨這外來政權的欺壓,雖然還不能將之推翻, 但能夠像這樣重重的一記耳光,讓他出醜難堪, 也算是出了幾十年來淤積在心中的一股怨氣。那種的感覺,只能用「 有夠爽!」一句話來形容,
因為和婉真走散,我想就自己搭車回去總部。走出中和運動場, 街上擠滿剛從造勢晚會出來的人群。大家都興高采烈,高談擴論。 擠在人潮之中,突然有人從背後拍了我的肩膀,我回頭一看,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為拍我的人,正就是郭倍宏。天啊, 這怎麼可能!但真的就是他,還是那張笑咪咪的臉, 毫無緊張氣色的站在我的面前。我張開嘴巴,有一千句話想要說, 但張口結舌,一句也講不出來。他也沒有說話,只是笑一笑, 和我握握手,然後轉身離開,消失在人群中。
我無法置信,自己竟會在人潮中和倍宏「不期而遇」。 甚至回到美國後,都還在懷疑自己,是不是興奮過度,產生錯覺。 直到1991年,倍宏來底特律訪問, 大家談到當時他如何離開現場的種種時,倍宏對我說,「 我在路上還拍了你一下肩膀,你忘了嗎?」我這才確認, 這不是我的錯覺。但我還是無法想像, 倍宏在那種危機四伏的情形下,竟能那麼鎮靜, 竟還有心情來和我打招呼,可見他真的有過人的才能與領袖的個性。 無怪他當年能在北卡的學生組織中脫穎而出,成為學生領袖; 又透過「海報事件」奔走全美,串連各地學生會,籌組「台灣學生」 ,隨後又出任「台獨聯盟美國本部」的主席;回台後, 繼續為台灣獨立運動努力,並在自己的專業上發光發熱, 以至被推選為「民視」董事長。
<後記>
在那場造勢晚會遇見了廖述宗教授與陳文彥教授, 使我對北美洲教授協會(NATPA)的印象非常深刻。 回到美國找到了教職之後,我立刻申請加入NATPA。 1991年12月廖述宗教授再次率團回台觀選,我也隨行。 同團的還有陳文彥教授,李雅彥教授和商文義教授。 我們抽空到土城看守所去探望回台被捕的張燦鍙, 以及第二次返台在桃園機場被捕的郭倍宏。
這次再看到他,我已經沒有悲情。因為「懲治判亂條例」已經廢止, 「行動100聯盟」也如火如荼的推動修正其母法「刑法100條」 。若是通過,他將無罪獲釋, 即可堂堂正正的在台灣推動台灣獨立運動, 或在自己的專業上貢獻台灣。他果然都做到了。
順便一提的是,1989年那場選舉,以「新國家,新國會, 新憲法」為號召的「新國家聯線」候選人全數當選,大獲全勝。 選舉結束那晚,我和太太帶著兩個小孩, 到師大夜市和陳婉真與黃華聚餐慶祝。 飯後我和婉真與黃華到別處繼續討論,太太則先帶兩個小孩先離去。 我回到家中時,太太驚魂甫定的告訴我,她搭計程車會家時, 司機突然告訴她,有輛車子一路從師大夜市跟過來, 一直要衝撞他的車子,似乎是要找麻煩。她回頭一看, 車裡坐的是兩名理這小平頭的男子, 立刻想到站在我家樓下那兩位便衣。 她嚇得趕快叫司機在一個人多的市場邊停車, 拉著兩個小孩躲入人群之中,那部車似乎還要繼續追撞, 她拉著幼兒,繞過小巷,一路跌跌撞撞的逃回家。 我向婉真提起此事,她說情治人員這次是灰頭土臉, 很有可能是要恐嚇一些人藉以出氣,這種事情以前常發生。 我不知道此事的真象,
但讓我連想到許多反對運動者無原無故遭到車禍, 甚至意外死亡的事件。1993年我在台北遇見王康陸先生, 約好過兩天到台獨聯盟辦公室去和他聊聊, 沒想到第二天他竟在陽明山遭到一起離奇可疑的車禍而喪生。 我到台獨聯盟辦公室去看他時,是舉香向他默禱。


Source from Mrs. Y. Huang / Houston 10/2016
Posted in 10/2016